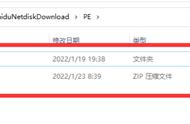城郊农村的纺织业“盛行于中南乡地方,但不过为农家的一种副业,很少专门经营的。其中又分纱帕业、织布业、制丝业、纺线业几种”。官渡一带“织纱帕的人家很多。这种工业,历来相传,民间自由纺织,没有工厂的设立,品质之佳,可与北平(北京)出产媲美”。后因“女子装饰渐渐改良,这种业务,也渐有退化的趋势”。滇池北岸“乡镇妇女,除了耕耘外,织布的最多,每年出品的数量也不少”,在官渡、小板桥形成了两个土布交易市场。“从前织布所用的棉纱,是由本地人用手工纺的,品质粗劣,不甚适用。自洋纱输入,纺纱工业就无形消灭,概用洋纱织成土布”,多半“仍是农家副业,现在还用土法” (见民国《昆明县乡土教材》等)。

此外,还有城西明朗、立章、白村的轧毡业,村民善于制作毡帽、毡子,“质虽耐久,但因式样古拙,行销不广”。城南的饵块营、城西的大鱼镇、张家乡村民又善于织席,产品有滑席、草席等,“可供全县之需”。此外,城南莲德镇清棚村的竹工,城北厂口的造纸,都有一定的特色(见民国《昆明县乡土教材》等)。
农村:“烟”“赌”危害大 男领孩子女下田
早年昆明农村社会问题也不少。有老人回忆:“旧社会的劳力,以男子为主,女子为辅,而昆明县则不尽然。因劳力有余而进城市,男子亦进城从事工商,或投靠衙门当书吏差役,获利皆丰厚于务农。除局部犁田翻地、车水赶车的必要男子劳动外,其余田间活计,家里劳作,多属女子。副业如卖菜蔬、瓜果、鸡鱼,亦多女子兼营。稍有余暇,不分城乡,出卖零工。一些男子,宁在家领小孩,间或而蹲茶馆,间或而困烟馆,间或而聚赌博、交匪人。女子一日劳动之所得,不够男子一日之吹;一年之积蓄,不够一夜之赌,流于破家荡产,作奸犯科,酿成农村万恶的社会,人所共见之。”(《昆明市志长编》)
民国初期,一“赌”一“毒”,都是昆明四乡的大问题。
先看“赌”。民国初年的《滇声报》说:“赌之为害,省城禁赌认真,赌徒不易藏身,因而撤之四乡。现闻各乡寨有多数赌徒,秘密开场,藉赌抽头,致使一般农家子弟,因赌倾家,流为盗贼者,时有所闻。”
再说“毒”。据城东郊区老人回忆,从20世纪 20年代到30年代初,当地“可说家家都种鸦片烟,约占当时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收烟后,有的拿到小板桥销售,有的是官渡的人来收购。村里的人普遍抽大烟。每个村子都有几家烟馆”。“男的几乎都吹上瘾。一两生烟,能换二升米。抽大烟的人,早上起不来,白天精神萎靡不振,搞不了劳动,还想吃点好的东西。晚上劲头出来,则专门用于生方设法变卖家具什物上,或者是去偷别家的东西”,“有的把田产地业吹光了,搞得倾家荡产”(见《昆明市志长编》)。
滇池湖畔的渔村和渔家

早年滇池边的渔村不少。昆明近旁有大观楼、明家地、西坝、海埂、五甲塘、清河;呈贡有斗南村、江尾村、乌龙浦;昆阳有坝埂村、亮沟村、大沟尾、大河嘴、白山村、有余村、老塘嘴、独房子;晋宁有安乐村、余家沟、黄家地、老荒滩、沙堤村、江渡、佛墩、河泊所、下海埂等。到20世纪中期,滇池周边约有渔民两千多人,昆明附近有五百多人,一百人户。其中绝大多数是半农半渔,专门从事渔业的很少,因为渔业收入低,不足以解决一家的生活问题。民国《续云南通志长编》称:“滇池渔民之生活,因受农村经济*之巨潮,日陷崩溃,故极宜设法挽救也。”坦言当时“渔民生活,受种种压迫,痛苦异常”,而“应如何改善渔民生活,废除苛税杂捐,普及水产知识”,都亟须解决。

旧时在滇池从事渔业的大小船舶约有三百多艘。使用的渔具主要是渔网,有用麻丝织成的篆网、麻遮线笼、线花篮、线网、丝网、撒网、挟网,还有竹制的篾笼子、篾花篮等。此外还有用罾网和水老鸹(水乌鸦)来捕鱼的。昆明城内外是滇池渔产最大的市场,其次是沿湖各县的县城。
当年昆明附近的草海上,渔船穿梭来往,渔民打得鱼后,装在木盆里,沿着大观河划到篆塘,有的在船边就出售了,有的直接挑到菜市上出售,还有的买给鱼贩子,鱼贩子再拿到城内市场上销售。昆明市场上售卖的主要是鲜鱼,也有腌鱼,主要是腌白鱼,还有旺季捕得太多一时卖不出去而腌制的其他鱼。
除了鱼类之外,滇池的水产品“还有水藻,经捞取晒干成饼状,用作肥田之用。计每饼重五六斤,每百斤售价十元左右。此项藻饼,一般农民呼为海粪,因含氮甚丰,故农民乐用。在滇池中可自由捞取,亦有专从事于此项海藻饼之捞取者。”此外滇池“渔妇捞取滇池中一种名为海菜之藻,腌以盐,加辣料、米散等,制为一种卤咸菜,以之佐食,名曰海菜酢。亦有专制以出售者”(民国《续云南通志长编》)。
砍柴烧窑:“黄窑”和“黑窑”
昆明远郊区山多,盛产竹木。“竹子有金竹、水竹、实心竹、千层竹、钓鱼刺、紫竹、刺竹、山竹,人面竹等种,其中以金竹水竹的用途最大,产量也最多。”“树木有松、栗、柏、冬瓜木、楸木、樟木、梧桐等种。其余的杂木,种类甚多,不胜悉举。”而城里对竹木的需求很旺,砍柴伐木就成了山区农民的一大副业。“但山区人民,不事研究种植,多听其自生自长,又复自由采伐,由此童山濯濯(秃山秃岭,草木全无),殊为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