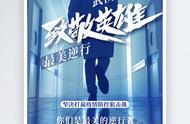《麦田里的反叛者》剧照。
1965年,塞林格公开发表了最后一篇作品《哈普沃斯,16,1924》,占据了当期《纽约客》绝大多数版面。这是一封来自西摩·格拉斯7岁时写给父母的一封长信。自此,塞林格再未公开发表过任何作品,也极少与外界往来。
塞林格的咒语
塞林格在1940年代末期开始接触到东方哲学。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战后的美国青年对传统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怀疑。关于“人生意义”的终极问题的答案在人们的眼中逐渐模糊。无法摆脱战争带来阴影的塞林格同样十分渴望一份心理的安宁,但是从他小说中提出的近乎偏执的问题看来,安宁并没有那么容易寻求。
1955年,塞林格发表了《弗兰妮》。

《玛丽·雪莱》剧照。
这部短篇小说中包含的问题十分尖锐,弗兰妮对于文学、自我、爱情的疑惑一步步将她推向崩溃的边缘,此时她又因一本书经历着信仰上的危机。塞林格持有的态度或许是悲观的。
“这群年轻小伙一开口都是清一色大学生知识分子的腔调,不管轮到哪个说话,没一个不拔尖了嗓子,一通慷慨陈词,就好像是在一劳永逸地解决某个极端有争议的问题,正是这个问题让大学外面的那个世界一筹莫展,已经瞎忙活了几个世纪。”
没有留下任何回答,甚至回答的尝试,小说以弗兰妮的昏厥戛然而止。第二部分《祖伊》发表于1957年,塞林格试图通过祖伊对于弗兰妮的开导来解释一种观念:天堂就在人的心中,而不在任何于自我之外的地方:“我们他妈的又笨又多愁善感又这么没有想象力,所以才看不到天堂”。孤掌何鸣?塞林格从《九故事》到《祖伊》中一直在试图给出他的解释。他在自己编造的迷宫中不停地寻找着一个出路,在《弗兰妮与祖伊》中,塞林格也给出了自己的一个说法。

《玛丽·雪莱》剧照。
塞林格的作品对于当下的人们来说,依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不仅仅是“经典作品“的光环,而是关于意义的困境在当下依然存在,甚至更为突出。互联网的发展、逆全球化的浪潮、去中心化技术兴起及贡献了众多科技奇观的人工智能都冲击着这一代的人们,没有人知道未来将要走向何方。许多在时代潮头的人们的手机上都有冥想软件,试图从已在硅谷风行多年的佛学,特别是禅宗中找到一些安宁,或者说是答案。
塞林格对于东亚的文化十分了解。在《抬高房梁,木匠们》的开篇,西摩用“伯乐相马”的故事哄弗兰妮睡觉。《西摩:小传》中对中国、日本古典作品的大量引用也表明了其对东亚文化的研究。对于东方文化,西方人通常认为这其中有着难以跨越的底层思维的壁垒。德国哲学家奥根·赫立格尔曾在日本学习禅,在他的记录《箭术与禅心》中,他写道:“禅理藏在不可见的黑暗中,就像是东方的精神生活所酝酿出来的奇妙谜语:无法解释而又无可抗拒地吸引人。”

《麦田里的反叛者》剧照。
百年之前人们的困扰和忧虑随着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减退,依然有许多获得世俗意义上成功的人们沉浸在身心灵的修行中,寻求一些他们也说不清的东西。于是直到现在,人们依然对塞林格充满着好奇和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