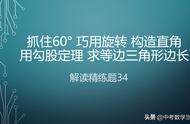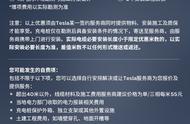在法国也是一样,他的和解既没有让自由派资产阶级满意(斯塔埃尔夫人称其为“马背上的罗伯斯庇尔”),也未能将保王党平息。1804年3月对当甘公爵的处刑,让保王党永远地将拿破仑和大革命划到了同一阵营。这一划分,也让英国有了理由再次向法国宣战,尽管1805年战端重启的根本原因是殖民地的经济冲突——法国重返安地列斯群岛对英国造成了威胁,但是英国则以“对抗革命的始作俑者,弑君者,敌宗教者”的名义在欧洲召集了新的联军对抗拿破仑。自打1814年和1815年,也就是皇帝倒台开始,拿破仑就变成了“暴君、*害欧洲青年的凶手、野心勃勃的佣兵队长”,或者夏多布里昂口中的“近代一切不幸的根本”。
借着回忆录重回法国
1815年拿破仑和他的帝国一起从欧洲大陆上消失了,为了避免麻烦,拿破仑的拥趸用“不在的人”和大写的“他”来代指他们的皇帝。

但是这一切因为两件事而有所好转,第一件是1823年《圣赫勒拿回忆录》的出版,它很快就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各国出售,拿破仑的形象也从暴君变成了在欧洲推广启蒙思想、用法国制度团结欧洲人民的先驱。《回忆录》也成了无数革命者、改革者的枕边读物,甚至远销拉美和埃及。资产阶级从中看到了对抗传统价值以重获失去的民族权利和特权的可能。

第二件事就是1840年路易菲利普一世迎回拿破仑遗体,尽管他的举动的目的是重新团结自由派,但是这次迎接让拿破仑的传奇和形象重新活了起来。甚至还出现了一些领导者给自己的小孩起名“拿破仑”。1851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政变再次终结了拿破仑在自由派人眼中的好印象。我们先不讨论第二帝国在1860s前后逐渐向自由派转向。路易·波拿巴的政变无疑再次激活了波拿巴党人与自由派甚至共和人士之间的恨意,这也使得一些历史学家致力于对一切拿破仑传奇(无论好坏)刨根问底,来对抗由官方主编的“历史”,这些人有亲自由派的温和保王人士(梯也尔)以及坚定的共和人士(儒勒·米什莱)。
战争背景下的拿破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