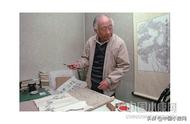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他的小说、散文、戏剧、文论、新旧体诗等,皆取得很高艺术成就,堪称文体家;又兼及书画,多有题跋,以博雅名世。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作家”。
2019年5月16日是汪先生逝世22周年的日子,我们从专题片《梦故乡》(江苏电视台摄制)中剪取出汪曾祺先生“出镜”的部分,汇成短片,献给喜欢汪先生的读者朋友。
汪曾祺视频影像资料
江苏电视台摄于1993年
在视频里,汪先生用一口民国老电影中的普通话“自报家门”,介绍自己的求学与工作经历,以及自己几部重要作品的创作背景。汪先生的口音、语调、谈吐、仪态乃至精神气质,都以影像的形式熠熠呈现,如在目前。这段视频,不知是不是汪先生存世的唯一一段视频。
最后,再附汪先生的两篇散文。
荷花
我们家每年要种两缸荷花,种荷花的藕不是吃的藕,要瘦得多,节间也长,颜色黄褐,叫做“藕秧子”。在缸底铺一层马粪,厚约半尺,把藕秧子盘在马粪上,倒进多半缸河泥,晒几天,到河泥坼裂有缝,倒两担水,将平缸沿。过个把星期,就有小荷叶嘴冒出来。过几天荷叶长大了。冒出花骨朵了。荷花开了,露出嫩黄的小莲蓬,很多很多花蕊。清香清香的。荷花好像说:“我开了。”
荷花到晚上要收朵。轻轻地合成一个大骨朵。第二天一早,又放开。荷花收了朵,就该吃晚饭了。
下雨了。雨打在荷叶上啪啪地响。雨停了,荷叶面上的雨水水银似的摇晃。一阵大风,荷叶倾侧,雨水流泻下来。
荷叶的叶面为什么不沾水呢?
荷叶粥和荷叶粉蒸肉都很好吃。
荷叶枯了。
下大雪,荷花缸里落满了雪。
《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
一个作品写出来了,作者要说的话都说了。为什么要写这个作品,这个作品是怎么写出来的,都在里面。再说,也无非是重复,或者说些题外之言。但是有些读者愿意看作者谈自己的作品的文章,——回想一下,我年轻时也喜欢读这样的文章,以为比读评论更有意思,也更实惠,因此,我还是来写一点。
大淖是有那么一个地方的。不过,我敢说,这个地方是由我给它正了名的。去年我回到阔别了四十余年的家乡,见到一位初中时期教过我国文的张老师,他还问我:“你这个淖字是怎样考证出来的?”我们小时做作文、记日记,常常要提到这个地方,而苦于不知道该怎样写。一般都写作“大脑”,我怀疑之久矣。这地方跟人的大脑有什么关系呢?后来到了张家口坝上,才恍然大悟:这个字原来应该这样写!坝上把大大小小的一片水都叫做“淖儿”。这是蒙古话。坝上蒙古人多,很多地名都是蒙古话。后来到内蒙走过不少叫做“淖儿”的地方,越发证实了我的发现。我的家乡话没有儿化字,所以径称之为淖。至于“大”,是状语。“大淖”是一半汉语,一半蒙语,两结合。我为什么念念不忘地要去考证这个字;为什么在知道淖字应该怎么写的时候,心里觉得很高兴呢?是因为我很久以前就想写写大淖这地方的事。如果写成“大脑”,在感情是很不舒服的。——三十多年前我写的一篇小说里提到大淖这个地方,为了躲开这个“脑”字,只好另外改变了一个说法。
我去年回乡,当然要到大淖去看看。我一个人去走了几次。大淖已经几乎完全变样了。一个造纸厂把废水排到这里,淖里是一片铁锈颜色的浊流。我的家人告诉我,我写的那个沙洲现在是一个种鸭场。我对着一片红砖的建筑(我的家乡过去不用红砖,都是青砖),看了一会。不过我走过一些依河而筑的不整齐的矮小房屋,一些才可通人的曲巷,觉得还能看到一些当年的痕迹。甚至某一家门前的空气特别清凉,这感觉,和我四十年前走过时也还是一样。
我的一些写旧日家乡的小说发表后,我的乡人问过我的弟弟:“你大哥是不是从小带一个本本,到处记?——要不他为什么能记得那么清楚呢?”我当然没有一个小本本。我那时才十几岁,根本没有想到过我日后会写小说。便是现在,我也没有记笔记的习惯。我的笔记本上除了随手抄录一些所看杂书的片断材料外,只偶尔记下一两句只有我自己看得懂的话,——一点印象,有时只有一个单独的词。
小时候记得的事是不容易忘记的。
我从小喜欢到处走,东看看,西看看(这一点和我的老师沈从文有点像)。放学回来,一路上有很多东西可看。路过银匠店,我走进去看老银匠在模子上敲打半天,敲出一个用来钉在小孩的虎头帽上的小罗汉。路过画匠店,我歪着脑袋看他们画“家神菩萨”或玻璃油画福禄寿三星。路过竹厂,看竹匠把竹子一头劈成几杈,在火上烤弯,做成一张一张草筢子……多少年来,我还记得从我的家到小学的一路每家店铺、人家的样子。去年回乡,一个亲戚请我喝酒,我还能清清楚楚把他家原来的布店的店堂里的格局描绘出来,背得出白色的屏门上用蓝漆写的一付对子。这使他大为惊奇,连说:“是的是的”。也许是这种东看看西看看的习惯,使我后来成了一个“作家”。
我经常去“看”的地方之一,是大淖。
大淖的景物,大体就是像我所写的那样。居住在大淖附近的人,看了我的小说,都说“写得很像”。当然,我多少把它美化了一点。比如大淖的东边有许多粪缸(巧云家的门外就有一口很大的粪缸),我写它干什么呢?我这样美化一下,我的家乡人是同意的。我并没有有闻必录,是有所选择的。大淖岸上有一块比通常的碾盘还要大得多的扁圆石头,人们说是“星”——陨石,以与故事无关,我也割爱了(去年回乡,这个“星”已经不知搬到哪里去了)。如果写这个星,就必然要生出好些文章。因为它目标很大,引人注目,结果又与人事毫不相干,岂非“冤”了读者一下?
小锡匠那回事是有的。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还记得。我那时还在上小学,听说一个小锡匠因为和一个保安队的兵的“人”要好,被保安队打死了,后来用尿碱救过来了。我跑到出事地点去看,只看见几只尿桶。这地方是平常日子也总有几只尿桶放在那里的,为了集尿,也为了方便行人。我去看了那个“巧云”(我不知道她的真名叫什么),门半掩着,里面很黑,床上坐着一个年轻女人,我没有看清她的模样,只是无端地觉得她很美。过了两天,就看见锡匠们在大街上游行。这些,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使我很向往。我当时还很小,但我的向往是真实的。我当时还不懂高尚的品质、优美的情操这一套,我有的只是一点向往。这点向往是朦胧的,但也是强烈的。这点向往在我的心里存留了四十多年,终于促使我写了这篇小说。
大淖的东头不大像我所写的一样。真实生活里的巧云的父亲也不是挑夫。挑夫聚居的地方不在大淖而在越塘。越塘就在我家的巷子的尽头。我上小学、初中时每天早晨、傍晚都要经过那里。星期天,去钓鱼。暑假时,挟了一个画夹子去写生。这地方我非常熟。挑夫的生活就像我所写的那样。街里的人对挑夫是看不起的,称之为“挑箩把担”的。便是现在,也还有这个说法。但是我真的从小没有对他们轻视过。
越塘边有一个姓戴的轿夫,得了血丝虫病,——象腿病。抬轿子的得了这种最不该得的病,就算完了,往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呢?他的老婆,我每天都看见,原来是个有点邋遢的女人,头发黄黄的,很少梳得整齐的时候,她大概身体不太好,总不大有精神。丈夫得了这种病,她怎么办呢?有一天我看见她,真是焕然一新!她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头发梳着光光的,衣服很整齐,显得很挺拔,很精神。尤其使我惊奇的,是她原来还挺好看。她当了挑夫了!一百五十斤的担子挑起来嚓嚓地走,和别的男女挑夫走在一列,比谁也不弱。
这个女人使我很惊奇。经过四十多年,神使鬼差,终于使我把她的品行性格移到我原来所知甚少的巧云身上(挑夫们因此也就搬了家)。这样,原来比较模糊的巧云的形象就比较充实,比较丰满了。
这样,一篇小说就酝酿成熟了。我的向往和惊奇也就有了着落。至于这篇小说是怎样写出来的,那真是说不清,只能说是神差鬼使,像鲁迅所说“思想中有了鬼似的”。我只是坐在沙发里东想想,西想想,想了几天,一切就比较明确起来了,所需用的语言、节奏也就自然形成了。一篇小说已经有在那里,我只要把它抄出来就行了。但是写出来的契因,还是那点向往和那点惊奇。我以为没有那么一点东西是不行的。
各人的写作习惯不一样。有人是一边写一边想,几经改削,然后成篇。我是想得相当成熟了,一气写成。当然在写的过程中对原来所想的还会有所取舍,如刘彦和所说:“殆乎篇成,半折心始”。也还会写到那里,涌出一些原来没有想到的细节,所谓“神来之笔”,比如我写到:“十一子微微听见一点声音,他睁了睁眼。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之后,忽然写了一句: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只是写到那里,出于感情的需要,我迫切地要写出这一句(写这一句时,我流了眼泪)。我的老师教我们写作,常说“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人不懂他这句话。我的这一个细节也许可以给沈先生的话作一注脚。在写作过程要随时紧紧贴着人物,用自己的心,自己的全部感情。什么时候自己的感情贴不住人物,大概人物也就会“走”了,飘了,不具体了。
几个评论家都说我是一个风俗画作家。我自己原来没有想过。我是很爱看风俗画。十六、七世纪的荷兰画派的画,日本的浮世绘,中国的货郎图、踏歌图……我都爱看。讲风俗的书,《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一岁货声》……我都爱看。我也爱读竹枝词。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我的小说里有些风俗画成分,是很自然的。但是不能为写风俗而写风俗。作为小说,写风俗是为了写人。有些风俗,与人的关系不大,尽管它本身很美,也不宜多写。比如大淖这地方放过荷灯,那是很美的。纸制的荷花,当中安一段浸了桐油的纸捻,点着了,七月十五的夜晚,放到水里,慢慢地漂着,经久不熄,又凄凉又热闹,看的人疑似离开真实生活而进入一种飘渺的梦境。但是我没有把它写入《记事》,——除非我换一个写法,把巧云和十一子的悲喜和放荷灯结合起来,成为故事不可缺少的部分,像沈先生在《边城》里所写的划龙船一样。这本是不待言的事,但我看了一些青年作家写风俗的小说,往往与人物关系不大,所以在这里说一句。
对这篇小说的结构,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以为前面(不是直接写人物的部分)写得太多,有比例失重之感。另一种意见,以为这篇小说的特点正在其结构,前面写了三节,都是记风土人情,第四节才出现人物。我于此有说焉。我这样写,自己是意识到的。所以一开头着重写环境,是因为“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人和事。有个青年作家说:“题目是《大淖记事》,不是《巧云和十一子的故事》,可以这样写。”我倾向同意她的意见。
我的小说的结构并不都是这样的。比如《岁寒三友》,开门见山,上来就写人。我以为短篇小说的结构可以是各式各样的。如果结构都差不多,那也就不成其为结构了。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汪曾祺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年1月出版
《汪曾祺全集》是汪曾祺一生所著所写文字的总集,收入迄今为止发现的汪曾祺全部文学作品以及书信、题跋等日常文书,共分12卷:小说3卷,散文3卷,戏剧2卷,谈艺2卷,诗歌及杂著1卷,书信1卷,并附年表,共计400多万字。
编全集是一个大工程,《汪曾祺全集》也不例外。我们努力了八年,前期制定编辑原则、体例,确定《全集》怎么编,同时物色、确定各卷主编人选;中期与主编、分卷主编协调工作、解决编校问题,并将汪家提供的和人文社征集的文章、书信陆续寄给各分卷主编;后期督导进度,完成编辑工作。在此过程中,发动社会力量辑佚钩沉,广泛征询专家学者对于《全集》编辑工作的意见,结合人文社的出版经验,最终打造出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汪曾祺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