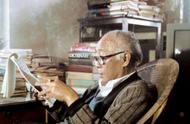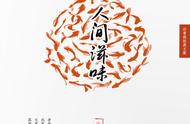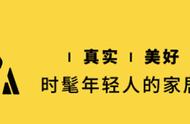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文|《小康》·中国小康网记者 赵狄娜
慈父、知名作家、美食家、生活家……汪曾祺的迷人之处甚多,汪家子女通过生活里的点滴小事,向我们展示了这位老头儿更加生动的一面。

作画 作者在家中作画,摄于1994年。图片/摘自《汪曾祺别集》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汪曾祺和其夫人施松卿合葬在北京西山下的福田公墓,墓碑碑顶保持了原石的天然起伏,这是长子汪朗的主意。石碑正面刻着“高邮汪曾祺”和“长乐施松卿”,背面无字,生平、著作都无交代。去年11月,汪曾祺的长女汪明病逝。今年为他扫墓的是年近七旬的长子汪朗、次女汪朝。
汪朝自带了一个装过洗衣液的空桶,接水时还咕噜噜冒泡,她用自带的刷子,就着水刷了墓碑基座的黄沙。墓碑被清扫干净后,汪朗将一瓶XO从碑顶浇下去,顿时酒香四溢。两人在墓前站好后,叫了一声“老头儿”——这是汪曾祺子女对他的称呼。
慈父、知名作家、美食家、生活家……汪曾祺的迷人之处甚多,汪家子女通过生活里的点滴小事,向我们展示了这位老头儿更加生动的一面。
做父亲,家庭中“没大没小”
1958年,年近四十的汪曾祺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的农业科学研究所。那时候,儿子汪朗还没上学,大女儿汪明5岁,小女儿汪朝3岁,都在幼儿园上全托。妻子施松卿在参加单位的军事训练,不许请假。没人送行,汪曾祺一个人去了沙岭子,一待就是三年多。
在张家口*都是体力活,曾经连体育都要补考的文弱书生汪曾祺,经过劳动能扛起170斤一包的小麦,走上传送粮食的厚木板,“哗”的一下将粮食倒入囤中。汪曾祺从没细说过当年劳动吃的苦,在文章中也是一笔带过。他甚至在散文《随遇而安》中,用调侃的口气说:“我这才知道‘劳动是沉重的负担’这句话的意义。”
汪曾祺把一生中最艰苦的劳动改造时期,过得很有诗意。汪家子女的记忆里,父亲在果园耐心地喷波尔多液,形容蓝色的波尔多液“颜色浅蓝如晴空”;他画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画完一种薯块就把实物放到牛粪火里烤熟、吃掉,甚至非常得意地想,全国能够吃这么多种马铃薯的人,没有几个。他写了小说《羊舍一夕》,还在农闲时候演戏,唱过小歌剧《三月三》,演的是里面的汉奸胡宝才。甚至,他给家人回信,用的是毛笔,还非要用鸡狼毫。初学拼音的儿子汪朗给父亲“拼”了一封信,逼得汪曾祺连忙现学拼音,好写回信。
大女儿汪明回忆,父亲每次回北京探亲,都乐呵呵地背回好些土豆、口蘑之类的特产。他和人们眉飞色舞地讲沙岭子的各种土豆,用家里的烟灰缸做点心模子烤黄油点心吃,还把沙岭子出产的甜菜熬成糖稀,给孩子们解馋。他用茄子馅儿包饺子,最后都煮成了一锅面片汤。甚至,他带回来过两只野兔子,把剥了皮的兔子放在案板上,抡圆了胳膊狂砍一气。兔子还没剁开,就遭到了楼下邻居的投诉:“汪同志,干吗呢?震得我们家屋顶上的灰都落在饭锅里去了!”汪曾祺从沙岭子回来的每一个日子,对孩子们都是难忘而甜蜜的。
小女儿汪朝眼里的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慈父,从不对孩子们发脾气。“从小到大,没有教训过我们一句,绝对平等。”汪朝结婚很晚,母亲施松卿为此急得睡不着,父亲汪曾祺却不怎么着急。一次父女聊天,汪曾祺问汪朝,想找一个什么样的。汪朝不假思索地说:“跟你一样的。”汪曾祺不禁笑了:“那你上哪找去!”语气里混合着几分自得和无奈。汪朝结婚前,心里有些忐忑不安地问父亲:“要是我结婚以后过得不好可怎么办?”汪曾祺的回答不假思索:“那就回来!”这句简简单单的话,一下打消了汪朝的犹豫,她“顿时觉得胆气壮了起来”。
脾气好、性格随和的汪曾祺,在家里一点“地位”都没有,和孩子完全平等。妻子施松卿叫他“老头儿”,三个子女这样叫,就连小孙女汪卉也这样叫。有时候外人来了,家人在言谈间,一不留神也常把“老头儿”冒了出来,弄得人家直纳闷。
这种“没大没小”,也是汪曾祺一直倡导的,他写过一篇《多年父子成兄弟》,说“我觉得一个现代化、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意思”。
儿女们成家后,回来团聚成了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随和厚道的汪家人都不欢迎客人。有时候,汪曾祺糊涂记错了日子,有约稿的编辑上门,一定会受到全家大小不友好的白眼。等客人走了,汪曾祺还会遭到大家的一致怒斥。汪曾祺辩解再三,会忍无可忍地用手比成两把手枪的样子,对着家人“砰!砰!砰!”几声,然后在一片笑声中落荒而逃,去睡午觉了。
过日子,爱吃又会“忽悠”
众所周知,汪曾祺爱做菜,用女儿汪朝的话说,“我爸在家里除了做饭别无所长”。
他讲究口味、火候,而且刀工也很棒。汪朝说他做的麻酱拌腰片用平刀片得飞薄,入口极脆嫩。他切肉丝,切得不粗不细。他会做煮干丝、拌菠菜泥、扦瓜皮、冰糖肘子、炒鳝糊、干煸牛肉丝、炒干巴菌。他在选材、配料、烹饪上都尽量依照当地风味。他出差云南,带来的特产是一包鲜嫩碧绿的豌豆尖。在北京住久了,他喜欢上了老北京的麻豆腐,每次做必须用羊尾巴油炒,配上刚冒出嘴儿来的青豆和干辣椒。汪朝记得,“这个菜最后往往倒掉,因为基本上只有他一个人吃。”
汪朝还记得自己同事来家里时,父亲在厨房忙活了半天,最后郑重其事地托出一盘蜂蜜蘸小萝卜来,削了皮,切成滚刀块,上面插满了牙签。这道奇怪的“果品”没人动,她向父亲抱怨还不如削几个苹果呢,谁吃不值钱的小萝卜啊。汪曾祺觉得很奇怪:“苹果有什么意思?这个多雅。”
汪曾祺讲究吃,和故乡高邮不无相关。跟随父亲回过高邮的汪朝感慨道:“高邮菜真好吃,高邮人真是讲究吃,食不厌精。父亲做的那些菜,拿到高邮来可坐不到头几把交椅。父亲从家乡得到了特别发达的味蕾,爱吃、会吃,各地的风味特色他都要尝试一下。其实他更感兴趣的,是美食后面的风俗习惯、地理人文等文化现象,这和他的文学追求有间接的关系。我母亲一辈子都不怎么会做饭。父亲做菜是责任,也是乐趣。我们喜欢吃什么,他都知道,看着我们吃他做的菜,他常常会露出一种满足的表情。”
子女们的记忆里,汪曾祺每天早上给自己煮一碗挂面,虽然没几根面条,但照样要精工细作。先卧个鸡蛋,溏心的,然后把剁细的葱、蒜、榨菜末、虾籽、郫县豆瓣放入碗中,加酱油、醋、香油、味精、胡椒粉,再兑一些开水,米放入煮得的面条即可。时隔多年,汪朝都记得面条的味道。“我们在他碗里尝一口,觉得好吃极了。星期天要求他给每人都做一碗,不行了,远不如他平时做的味道好,像是从精品变成了粗品。他也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
汪曾祺还爱逛菜市场,他说过:“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通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一次搬家,到了新家的胡同口,早市还有一会儿才散。他捧着一盆水仙花,挤到肉摊前大声问:“猪心多少钱一斤?”急得忙着搬家的子女们一把把他拽回来:“老头儿,家里的冰箱还没运进来呢,别瞎买!以后天天都有早市。”搬完家后,汪曾祺每天拎着一个脏兮兮的菜筐去买菜,饶有兴趣地四处看看。买菜以外,他还买过一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一个三块钱的放大镜,一尊一块钱的香炉(当烟灰缸)、一对不知多少钱的小瓷罐,有一回还抱回一个玻璃鱼缸和用塑料袋装着的两尾金鱼,放在病中的妻子床头茶几上给她解闷。他见过好玩意,买这些不值钱的小东西,目的很单纯——好玩。
汪曾祺喜欢花鸟虫鱼,写过一篇散文《草木虫鱼鸟兽》,但根据其子汪朗回忆,他只是“会忽悠”。汪朗曾在采访中吐槽父亲:“他文章里写得都挺有味道的,但实际生活中,他都做得不怎么样。他写了很多草木虫鱼,但实操水平是很差很差的。比如说养花吧。我们家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花,不像他写的老舍先生,一下养几十几百盆花,自己很精心地侍弄。印象里,原来就是大概每年要买一盆花,就是入冬的时候买一盆兰花,也就三五块钱,但从来也没开过。兰花刚来的时候,叶子还挺长,养两天尖儿就黄了,他就拿剪子剪下去了,越剪越短,养到最后花的命运就是枯萎了,我家花的命运都挺悲惨的。”母亲施松卿养花技术也在被吐槽之列,汪朗亲眼看到过,老太太用泡过假牙的水浇花。“那花也是有感情的,你这么对它肯定得死。”

其乐融融 作者一家在北京中山公园。图片/摘自《汪曾祺别集》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当作家,心怀温情和悲悯
60岁开始重写小说的汪曾祺,名气大了后,没有脱离生活,没有忘记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他跟最基层的老百姓交朋友,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并把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和事都写到了书里。但他并不总是冲淡平和的,遇到不平之事也会拍案而起。
汪朝回忆:“当时我们楼里一个开电梯的小姑娘被一个住户打了,我父亲非常生气,认为应该让打人者道歉。汪曾祺拉了两个老街坊主持正义,让小伙子当众向小姑娘认错。这事最后没有结果,因为打人的是一个蛮不讲理的愣小子。父亲把这件事写进散文《胡同文化》里,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汪曾祺很生气,“怎么可以打一个女孩子呢!”
汪曾祺很喜欢两句宋诗:“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他的身上一直充满着善良、悲悯和人文精神。汪朝说:“他的平民意识除了来自于自身性格和家庭影响,还有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受到的民主、自由风气的影响。父亲虽然是个老作家,创作跨越现代、当代两个文学领域,但他从不以‘老’自居,思想一点都不保守,他在文学界有很多年轻朋友。他给一些他认为有前途的年轻作家写评论、写序,为他们推介。他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为他们开路。父亲的文化底蕴、文学修养我们是望尘莫及的,但他和母亲那种心境平和、待人平等,不以己悲、不以物喜的生活态度对我们有很深的影响。”
汪曾祺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名篇《受戒》《大淖记事》曾深深影响着一代人,清新的文风开创着一个时代的先河,作品字里行间展现了高邮的水乡风光。实际上,汪曾祺19岁离开家乡,再回乡已是61岁的老人。在生活中,他很少谈到高邮。只有从他的作品中,子女们才知道家乡是什么样子。
“父亲的记忆力惊人,小说中的一些精微细腻的描写,非常生动准确。40多年后写出来的故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不差分毫。而且汪曾祺不善于虚构,他的人物、事件都是有原型的。这让一些家乡人也觉得不可理解,所以有人问,他是不是老带着个小本本,把什么都记下来。其实父亲是个很马虎的人,很少记笔记。父亲的作品中,很大一部分是写家乡的。最精彩的多在这一部分。有一些题材,他年轻时写过,到了老年,对人生有了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又重新写,他对家乡充满了感情。可以说,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知道和了解高邮的,是汪曾祺。”汪朝说。
在家里和孩子们聊天老被“挤对”的时候,汪曾祺会不服气地嚷嚷:“你们对我客气点,我将来是要进文学史的!”可孩子们笑得更厉害了:“老头儿,你别臭美了!”汪曾祺也不生气,他会跑到自己那间只有八九平米、到处堆着书和稿子的书房兼卧室里。这间陋室,是他写作的天堂,身处其中时,他恬然而满足。
去年是汪曾祺诞辰百年,汪家兄妹也度过了忙碌的一年。头发渐白的汪朗,眉眼像极了父亲,他参加了很多纪念汪曾祺的活动,接待了更多关注到汪曾祺、喜欢汪曾祺的人。爱汪曾祺的一群出版人、专家、学者,花费了一年多,打磨出了一套轻薄漂亮的集子——《汪曾祺别集》,他们请汪朗担任这套书的主编。
书送到汪朗手上时,他摸着书皮上的马蒂斯剪纸,说:“父亲如果在世,看见这套书一定也很满意。”他露出和汪曾祺一模一样的笑容,让人觉得那个好玩的老头儿又回来了。
(《小康》·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本文刊登于《小康》2021年9月下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