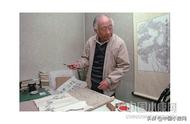·林日暖·
在人们对汪曾祺小说、散文、剧本甚至评论里的盎然诗意津津乐道、大加赞赏的时候,却几乎集体忽略了这些作品背后站着的“诗人汪曾祺”。
诗歌写作持续一辈子
汪曾祺的新诗,从1941年的《自画像》,到1993年的《我的家乡在高邮》,有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史。如果加上旧体诗和其他文体中散见的诗句,以及参加社会活动中的诗意表达,他的诗歌写作可谓持续了一辈子。
早在西南联大就读时,汪曾祺就是一个诗人。1992年,汪曾祺接受马原采访时曾回忆:
有一次我在我们西南联大的校园看到前面两个人说,谁叫汪曾祺呀,另外一个人就回答,就是写那首别人不懂他自己也不懂的诗的那个人。
年轻的汪曾祺不仅有诗人之名,更有诗人之实。在1941年的中国诗坛,“汪曾祺”是个闪光的名字,21岁的他写下了许多譬喻新奇的诗篇,如:“打开明瓦窗,/看我的烟在一道阳光里幻想”;“我一手拿支笔,/一手捏一把刀,/把镇定与大胆集成了焦点,/命令万种颜色皈依我的意向,/一口气吹散满室尘土,/教花布为我的眼睛心寒”……从中可见明显的西方现代派的影响。
汪曾祺开始写新诗的1940年代,其实也是九叶诗人非常活跃的年代。汪曾祺与九叶诗人中的多位年龄相仿,诗歌创作的起步时间也很接近。他与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等都曾是有诗歌交集的“西南联大人”,他们不仅是校友,还是同学,他们都受到过艾略特、里尔克、奥登等西方现代派诗人的影响。西南联大曾经有一个冬青社,汪曾祺、穆旦、杜运燮都是其中的成员;还有一个“文聚社”,办的刊物《文聚》也发表过汪曾祺和九叶诗人的作品。汪曾祺作的许多新诗比起九叶诗歌也毫不逊色。九叶诗人唐湜在《悼念曾祺》中写道:
(当年他)给我们的流派刊物《中国新诗》也写过篇散文诗《疯子》。如果我们的刊物不遭查禁,他可能会如他的同学穆旦、杜运燮、郑敏们一样,常给我们写稿,成为“九叶”或“十叶”中的一员。
新中国成立后,汪曾祺写少数民族题材的诗歌,像组诗《旅途》等,艺术上与闻捷的一些作品难分伯仲。黄裳在《也说汪曾祺》一文中,推崇汪曾祺的《早春》,认为“这是典型的‘朦胧诗’,如先为评家所见,无情棍棒怕不是落在杜运燮头上了”。
诗作与小说散文一脉相承
汪曾祺未编年小说《梦》开头的一首小诗这样写道:
给我一枝梦中的笔,/我会写出几首挺不错的诗。/可惜醒来全都忘了,/我算是白活了这一趟了。
可见他有着“诗歌情结”和“诗人情结”。他谈论自己的创作时,曾多次提到诗:
散文诗和小说的分界处,只有一道篱笆,并无墙壁(阿左林和废名的某些小说实际上是散文诗),我一直以为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散文诗的成分。
一个小说家,即使不是彻头彻尾的诗人,至少也是半仙之分,部分的诗人……小说之离不开诗,更是昭然若揭的……一个真正的小说家的气质也是一个诗人。
他早期写的是新诗,后期主要写旧诗。他的文字多为随心之作,无事不可入诗,有酬赠诗、自寿诗、忆旧诗、游踪诗、联语等。《辛未新正打油》中既有“宜入新春未是春,残笺宿墨隔年人”的工雅之语,更有“老夫亦有闲筹算,吃饭天天吃半斤”的打趣之言。“野餐得野趣,山果佐山泉。人世一杯酒,浮生半日闲”,这样的文字闲趣中见清雅,放达中见沉思。
汪曾祺的很多诗作与他的小说和散文一脉相承。1941年的新诗《自画像》中已有了“用绿色画成头发,再带点鹅儿黄,/好到故乡小溪的雾里摇摇,/听许多欲言又止的梦话”的诗句,其后许多自寿诗中也揭示了故土、往事对汪曾祺的重要意义,如“近事模糊远事真,双眸犹幸未全昏”等。儿时、故乡、远事成为汪曾祺丰厚的文学土壤,不仅小说及散文中常持一种回望的姿态,许多诗也是忆旧诗,如《江阴漫忆》《重来张家口》等。
汪曾祺很喜欢读宋人笔记,他的诗歌往往也是一小幅精工的风俗画。称汪曾祺为“生活家”“生活诗人”,实不虚也。他本人是极有烟火气的,喜爱研究饮食文化,也喜欢亲手烹饪,诗中自然少不了吃食:
淮南治丹砂,偶然成豆腐。馨香异兰麝,色白如牛乳。
擀面条的声音,/切白菜的声音,/下雪天的声音。/这种天气,怎么出去买菜?/卖菜的也不出摊。/楼上楼下,/好几家,/今天都吃热汤面。“牛牛!牛牛!/到副食店去买两块臭豆腐!”
中国当代诗人对古典诗歌的继承,最多只在内容里残存些许气息,对于形式则大都望而却步,汪曾祺却是个例外。自1960年起,汪曾祺的古体诗一直写到晚年。他有五首吟咏现代文人雅事的旧体诗《读史杂咏》,写的分别是何其芳、废名、林徽因、沈从文、周作人。写何其芳的一首是:“鼙鼓声声动汉园,书生掷笔赴烽烟。何期何逊竟垂老,留得人间画梦篇。”吟咏废名的一首是:“孤旅斜阳西直门,禅心寂寂似童心。人间消失莫须有,谁识清诗满竹林。”
汪曾祺对何其芳的称道与九叶诗人相当一致,但对废名“禅心寂寂似童心”的接受则远远超过九叶。同九叶诗人对话时,汪曾祺说:
你们能不能把外国的现代派变变样,把它中国化了。我说,你们写现代派的诗,是不是用现代派的手法写些中国诗、中国词,写一写我这一行——京剧。他们说,这我们办不到。因此,我就对他们不服。我主张,现代派也要中国化。
汪曾祺擅长书画,创作了许多题画诗。“种菊不安篱,任它恣意长。昨夜落秋霜,随风自俯仰。”汪曾祺画花,也咏花,诗中怡然自得、飘逸洒脱、恣意生长、别具一格的花,同样也是汪曾祺自己人生况味的写照。题画诗不仅出现在真实的生活中,也出现在汪曾祺的小说里,如《鉴赏家》中季匋民为红莲图所作的题画诗:“红花莲子白花藕,果贩叶三是我师。惭愧画家少见识,为君破例著胭脂。”
一生的底色汪曾祺早期诗歌、小说、散文中都有西方现代派的影子,到了后期,“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成为他自觉的创作指针。正如汪曾祺在诗中所概括的那样:
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里,抒情其华。有何风格?兼容并纳。不今不古,文俗则雅。

汪曾祺对文学有一种超功利的审美追求,他的文风散淡清新、不事雕琢、渲染理想人性,有家庭环境和地缘的影响,也有个人性情禀赋的影响。汪曾祺也有年轻锐气时,后来渐渐与世界、与人生和解,是以写出除尽火气、天然去雕饰的作品。
诗歌是汪曾祺一生的底色。汪曾祺说:“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汪曾祺是当之无愧的“文体家”,《看水》《受戒》《大淖记事》《天鹅之死》等众多小说,《葡萄月令》《淡淡秋光》等大量散文,当中都有直接的诗句和诗性的段落。汪曾祺主动性的文体尝试起步很早,1940年写作初稿、1946年定稿的《复仇》中有如下的句子:
人看远处如烟。
自在烟里,看帆篷远去。
来了一船瓜,一船颜色和*。
一船是石头,比赛着棱角。也许——
一船鸟,一船百合花。
深巷卖杏花。骆驼。
骆驼的铃声在柳烟中摇荡。鸭子叫,一只通红的蜻蜓。
汪曾祺的诗人身份是他多文体创作都具有“诗性”的原动力和坚实保障,是理解他诗化文学的珍贵密钥。汪曾祺的诗与诗化努力,是他受到古今中外诗歌教育之后的独特书写,从文字、理想到他自己,都是一种“诗意的实现”。诗人,才是他本质性的、终极意义上的文化身份。 (摘自《文学自由谈》202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