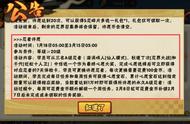昨天晚上,丈母娘又送了一瓶刚刚晒好的菜脯。新鲜的菜脯个头不大,层层叠放,上面还加了层白糖。打开盖子早已垂涎三尺了,拿出一条塞进口中,一嚼一声响,很是鲜脆,就是还没出油,少了菜脯特有的香味,要封存一段时间后再吃,那时候油乎乎的,香味十足,就更好吃了。上次丈母娘送的一瓶,是上个年度晒的,我几乎当零食吃了。每天回到家里,都会拿出一两条菜脯,放到嘴里嚼上一嚼,那滋味绝不逊于零食。以前,说到菜脯、咸菜,小孩子都很讨厌的,而如今,菜脯、咸菜可都是宝,几乎成了珍馐美馔的必备佐料了。不曾想儿时的菜脯粥、菜脯饭倒成了现在的香饽饽了……
记得小时候,家里买了“肪朥”(肪朥,潮州也叫朥纱,猪的脂肪肉)“白肉”来“热朥”(热朥,意思是炸猪油)。热朥后,为了别浪费,就会切点菜脯、葱花下鼎热炒一下,再下点稀粥,就成了香喷喷的,兄弟姐妹都争着吃的菜脯粥了,直到把竹花碗底都舔了个干净为止。
而菜脯饭,我则更是印象深刻。有一次,母亲和妹妹去外婆家做客,一去就住了十多天,记得是清明节后去的,准备端午节前后要回来。母亲娘家是客家的,路途遥远,平常都是要到潮州坐轮船去的。那一次却是坐车回来,要到枫溪车站去接。那一天,父亲提前做了饭,十点多就焖了一锅干饭,然后炒了菜脯,与干饭搅拌在一起,吃饱了就出发。父子两人各踩了自行车,在枫溪车站等到最后一班车到达,还没等到母亲和妹妹,只好悻悻而回。第二天,还是提前吃了菜脯饭,又是准时骑车到达,等到太阳下山了,还是没有接到人,我都有些心急了,会不会出了什么意外?父亲倒是很沉得住气。那时候没有电话,更不用提手机了,都是靠书信来往,一来一去,至少也得半个月,很是不方便。到了第三天,我都不想跟着父亲一起去了。而父亲放心不下我,还是敦促我一块去。依然还是菜脯饭,吃得饱饱的,仍然提前来到车站,好几趟班车都到了,踮起脚尖四处张望,还是没有没有母亲和妹妹的身影。天气又很炎热,加上菜脯饭又咸又干,也没有半点汤水下肚,晒得整个人口干舌燥的,只对着雪条摊直流口水。等到下午三点多,终于见到母亲和妹妹下了汽车,那个开心真的是无以形容了。因为很开心,也为了在母亲面前表现一下,我执意用自行车载着母亲,父亲则载着妹妹,一路从枫溪骑车回来。我还是第一次骑车载人走这么远的路,一路上顺顺利利的,快到村口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刚好很多人去看赛龙舟回来,整条路显得有些狭窄,加上车技还不过关,人又饥渴疲乏,在公路上一个不小心,车头一扭,没有把住,整辆车冲向路面的菜园,连人带车都倒在园地上,幸好没有摔伤。离家也就十多米远,真是扫兴,还出了这么个意外。因为连续三天午餐都是菜脯饭,加上摔了一跤,从而印象非常深刻。
那时候,菜脯粥、菜脯饭没有现在这么丰富的。除了粥和饭,菜脯就是主料了,炒了点油就成了。现在则有香菇、肉丁、虾米……菜脯只是佐料,爆炒起来那是香味十足的。现如今的菜脯,那可是厨师必备的佐料的,什么炒粿条、炒饭、炒菜、汤水、炒石螺、炒蛋、蒸肠粉……都非菜脯不可,菜脯的用处真的说不完。
菜脯这么好,那它是怎么制作的呢?其实很简单,菜脯就是腌“菜头口”(萝卜干)。冬月的白萝卜又肥又大,一个个像胖乎乎的小孩,拔出来洗干净了,晾干之后,拿出“揉粿钵”(揉,潮音读qi7,用手掌揉捏的意思,上世纪70年代,潮州农村每家每户都有一个揉粿钵),买来几斤粗盐,然后就可以来腌制菜脯了。把大个的菜头(萝卜)切块了,小个的就一整个下去,铺满了肉粿钵,就抓两把粗盐下去,双手撑开了,像打太极一样,把新鲜的菜头和粗盐在钵里充分摩擦,让盐渗透进菜头里,觉得差不多了就捞起来放到竹筐里,层层叠压。第二天,太阳出来后,就要把这些腌了盐的菜头拿出来晒,晚上再收回来。如果要咸一些,第二天晚上还会继续在揉粿钵里下盐揉擦菜头。然后就一直晒太阳,直到成为菜脯。晒干了的菜脯要赶紧装进钵仔里,那时候,每家每户都有很多瓶瓶罐罐的钵仔,很是漂亮,专门用来装菜脯和咸菜的,装好菜脯的钵仔要密封好,过上一段时间后,菜脯就会发出特有的香味。据说菜脯越老越好吃,而且还能消食健胃呢!我是见过放了二十来年的老菜脯的,乌黑油金发亮,散发出浓郁的香味,有很好的看相,但吃起来没有嚼劲,几乎是入口就化,老年人比较喜欢的。
小时候,肚子经常是饥肠辘辘的,说真的,尽管我非常喜欢吃菜脯粥和菜脯饭,但还是不大喜欢单纯以菜脯作为佐餐配料的,而现在,白粥和菜脯成了我的绝配,我都能把菜脯当成零食吃,真的匪夷所思啊!菜脯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见证了我们美好生活的来临,更佐证了我们幸福美好的新时代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