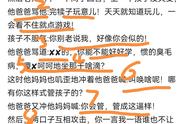吾乡地处豫中平原,旧时冬春时节,红薯可当半年粮,红薯叶更是离不了的当家菜。下面条当随锅菜,拌面蒸着吃,煠后生调,热炒下饭,晒干熬菜,腌酸红薯叶,每一种吃法,都关联着河南人的往昔生活,勾起了心心念念的美食记忆。

梁永刚| © 撰文
西瓜| © 版式
01
红薯叶,得打
▼
乡谚说:陆月陆,红薯鸡蛋一般粗。农历八月十五前后,一地红薯初长成,能刨着吃了,吾乡称为“刨青”。
红薯个头不算小,但是没有发育好,有些艮,不面也不甜,吃到肚里,容易憋胀。
乡人偶尔刨掘几块,往往连红薯秧也带回家,当饲料,喂牲口。此时的红薯叶太嫩,梗也软,青气未褪,不好吃。再说了,红薯一天不熟,红薯叶输送养料的使命就不算完成,吃早了,怕减产。
吾乡词典里,采摘各种农作物的叶子,用的动词不一样,譬如,采摘芝麻叶用“打”,洋槐叶用“捋”,萝卜叶用“拧”,玉米叶用“刷”,石香叶用“掐”。

红薯叶连着梗,梗连着秧,采摘时,左手捏着一根红薯秧儿的顶尖,掂起来,右手握着空拳,自上而下,用力猛打,靠着惯性,把一溜儿红薯叶采入手中。采摘红薯叶,和打芝麻叶有几分相似,故而乡人称之为打红薯叶。
寒露节气前,红薯尚未完全成熟,虽说也有人打红薯叶,但都是少量,解馋尝鲜而已。
男人们田间劳作归来,途径自家红薯地,顺便割捆红薯秧儿,背回家,主妇打下红薯叶,下面条,蒸蒸菜,炒梗吃,当一家人的菜蔬,剩下那些光秃秃的秧子,或铡了喂牛,或切段喂猪,或剁碎喂鸡,成为大小禽畜的重要饲料。
也有一些村妇,临做饭时,一看手头无菜,便跑到附近地里,打把红薯叶救急。

若是当天打当天吃,或者打一把吃一顿,红薯叶要挑选鲜嫩的,如果太老,口感不好。至于辨别老嫩,每一个乡野村妇都有自己的独门秘笈,正所谓“*猪*尾巴,一个人一个*法”。
有人善于观色,来到田间,先低头查看红薯叶颜色,颜色愈深,叶越老,梗越硬;有人用指甲掐,不是掐叶,而是掐梗,梗掐不动,叶吃不成;也有人凭经验,长长一条秧儿,离顶尖近的红薯叶,自然就嫩,反之,挨着根部的就老。
02
打红薯叶,颇有讲究
▼
打红薯叶的最佳时节,是在寒露后、下霜前,既不影响红薯长粗长壮,又能使叶子不经霜保持绿亮。
秋渐浓,霜未降,离刨掘尚有一段时光,但红薯已经过了生长旺季,密实茂盛的秧儿,匍匐一地,只待采收。
经霜后的红薯叶也是能吃的,味道还不错,吾乡谓之“霜打红薯叶”,只是颜色黑乌,有些发蔫,若是腌酸红薯叶,还是霜前青绿的好。
下霜前两三天,打红薯叶的人最多。
平常打,多是零零星星,随打随吃,不晒不存。
这时候打,阵势大,效率高,老的老,小的小,都带着家伙什,胳膊㧟的是竹篮,手提溜的是箩头,腋下夹着的是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