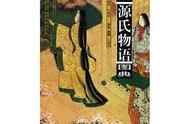2022 年 6 月 14 日,曾经「世界最大的海上餐厅」珍宝海鲜坊离港维修,在离开香港时,船东向公众「送上至诚的祝福,愿明天更好」。5 天后,在风浪中,这艘船在西沙群岛附近沉没,长眠于 1000 米深海底。媒体对这艘歌堂船的命运如此关心,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间富丽堂皇的餐厅,也承载了香港流行文化的隐喻。作为《食神》《无间道 2》《龙争虎斗》等一众电影的取景地,它见证了香港影视流行文化的兴衰。当然,在廖传喜眼里,沉船激起的还有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
1960 年代,廖传喜揣着家人东拼西凑的 360 块钱到达香港时,就是生活在避风塘。那时香港渔民或水上人的后裔为躲避台风侵袭所建的避风塘分布在香港仔、铜锣湾、筲箕湾、油麻地、鲤鱼门、九龙湾、观塘等地。随着娱乐业和餐饮业的兴起,这些避风塘也成为有别于主流香港文化之外的另一番风景 —— 前来消费的人享受歌舞升平,而定居于此的人也以服务业起家谋得生计。在翻译家陈实女士的诗文集中,有一段早期香港避风塘的记录:
艇,是谋生工具,也是家。是香港避风塘,不是金陵秦淮河。夏天入夜后,这里也有管弦丝竹,也有人浅斟低唱,然而歌女卖歌,不卖色笑;饮客或者为贩夫走卒,不着绫罗,席上亦不见珍馐。月还是汉唐的月,而风中隐含未散尽的硝烟,不再清了。先生,要艇吗?

1950 年代香港仔海傍,已有珊瑚酒家、太白海鮮舫等知名餐馆,餐饮业和娱乐业逐渐兴起。© Pinterest
对廖传喜而言,这样的繁华既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
1968 年,他在铜锣湾避风塘租得一艘小船,做起了炒香辣蟹的生意。廖传喜回忆:「那时候跟我们一起生活的,既有大陆和香港的渔民,也有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的渔民。同样是吃水产,各个国家的做法有很大区别。」虽然如今香港喜记的总店里,悬挂着蔡澜先生题写的「蟹皇」二字,无数食客也把这里当作避风塘菜系的发源地,但廖传喜始终认为,曾经的避风塘炒蟹是文化交融的结晶。当年在避风塘有三家摊贩做香辣蟹,除了喜记,另外两家是汉记和妹记,各家的做法不尽相同。至于现在为人熟知的金蒜版本,是他结合当年避风塘的各国渔家风味不断改良的成果。
对于出生于 1960 年代的香港漫画家、作家欧阳应霁先生来说,避风塘炒蟹中最让他食指大动的,是作为配角的金蒜。因为,这些金蒜让「蒜头性格中强悍厉害的一面表露无遗」。据欧阳应霁回忆,他印象中最早的避风塘炒蟹用的味料是豆豉、蒜头和辣椒:「豆豉先浸水去咸,捣烂加进蒜头同起锅,再加入辣椒干和鲜辣椒与硕大的越南蟹一同兜炒。而为了迁就岸上人的口味,上岸后的避风塘菜才演变成现在的金蒜版本。」

1971 年 10 月 30 日,珍宝海鲜舫在开业前 6 天发生大火,造成 34 人死亡、42 人受伤。© Pinterest
1971 年 10 月 30 日,就在香港仔避风塘的珍宝海鲜舫开业前 6 天,船只意外起火,还未正式开业的餐厅付之一炬。这件事不仅让这座举世瞩目的餐厅易主,也加大了政府整治香港避风塘的决心。20 世纪 70 年代,避风塘已经成为香港最负盛名的娱乐场所之一,但由于船上难以妥善安置抽水马桶和垃圾收集设施,大量食物残渣倾倒海内,卫生状况也日趋恶劣。
著名编辑叶灵凤先生逝于 1975 年,但从他的回忆录里依稀能发现当时的香港政府已有改造铜锣湾避风塘的打算。叶灵凤写道:「最近香港政府发表了填塞铜锣湾避风塘,改建体育场的计划。这事若实现,则自渣甸仓直至七姊妹一带的海岸形势,又要有剧烈的变化。」香港仔避风塘的那场火灾,以及全港避风塘的排污通弊共同推动了改造进程。1990 年,吴冠中先生的速写《香港避风塘》也成为大家对香港避风塘千帆相竞场景的最后追忆 —— 此时铜锣湾避风塘的对岸,已是高楼林立,贝聿铭先生设计的香港中银大厦在五年间拔地而起。
据廖传喜回忆,从 1980 年起,香港政府就不再发放熟食牌照。而曾经的两位竞争者也都年逾八旬,不再有子女接班。随着船家陆续上岸,廖传喜也用木头搭出一辆推车,将炒蟹的摊位搬到了马师道的天桥桥底。此后的 15 年里,无论风吹日晒,从晚上 8 点到凌晨 4 点,食客一定能在夜幕降临时看到廖传喜在桥底炒蟹的身影 —— 虽然仍名为喜记,但大家却更愿意以地名相称,这就是「桥底辣蟹」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