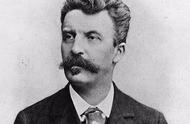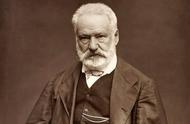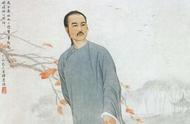北京土话说出来,总得让人怀疑说话的人是不是憋着一肚子坏水儿。世间一切深沉、深刻、深情、深邃,用北京人的嘴演绎一遍,都能被消解成不着调的玩笑。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这一听就是康河的柔波。
悄么声儿地哥们儿颠儿了,就跟我悄么声儿来的时候一样;甩甩我内俩袖子,连片儿云都特么带不走嘿!
这肯定是万泉河臭水沟子。
微博网友曾经实名要求北京人不要再翻译外国文学了,洋人说话都有了卤煮味儿。

他们估计是没看见王朔用北京话翻译的《金刚经》,当公元 994 年前的佛教经典被翻译成《连金刚那样坚固都能打破的通向彼岸的智慧》,就立马显得贫不喽嗖的,哪儿还有点儿宇宙大智慧的庄严感:
要是有人说:如来刚才好像来过这儿了,好像又走了,好像坐了一会儿,好像还躺了一会儿,这是人们故意拧巴我。为什么这么说?什么叫如来?既无地方可来,又无地方可去,所以叫如来——如同来过!
若有人言: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是人不解我所说义。”“何以故?”“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
如来是说真话的人,说实话的人,有时不得已才打比方有点车轱辘话的人,不编瞎话的人,不装神弄鬼的人。
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
读着这位佛祖的真言,总觉得是葛优在极乐世界开了讲坛:

2
北京是一个可大可小的抽象概念。
外国人把“北京”作为中国政府的代名词;外地人觉得,只要与北京搭边儿的地方都是北京;在北京郊区的原住民眼里,北京市区才叫“北京”,进市区也叫“上北京去”;而本土老北京认为,二环以里才是真正的北京。
四九城里,皇城根儿下,也有一条泾渭分明的阶级 & 地域鄙视链,老话叫“东富西贵,南贱北贫”。

在过去,北京西边上风上水,王府园林多,权贵也多;东面呢,粮仓廪实,漕运发达,富豪聚集;南城三教九流混杂,举子多、戏子多、窑子多;而北城新街口、德胜门一带,是八旗下层兵丁及其家属的居住区,地处偏僻,交通商业都很凋敝。在当时,看一个人家儿有没有身份,从说话就能听出来。
虽说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区别不大,但各区在口音上也有区别,有“西正东杂、北硬南滑”的规律。所谓“京腔京韵”,指的是内城使用的典雅官音,已经接近于标准普通话:语调平缓、不急不慢、字正腔圆、韵脚清楚、很少用俗语。康熙年间,皇上就要求所有官员必须说官话,宗室子弟也要讲官话,绝不能带进市井的油滑味儿。在后宫中,皇后和太妃们也用近乎京剧念白的普通话讲话,只有太监才说一口碎而贫的京片子。
现在热传的网红北京话,很多就是南城镶蓝旗宣武地区的胡同儿音、天桥儿音,老舍说“这腔调有时候过于轻脆快当,以至有时候使外乡人听不大清楚。”南城北京话的特点是语速快、吞音多、俗语多、有江湖气,在过去被官宦家族认为是惫懒油滑的象征,或是家教高低的表现,不过现在倒成了北京人的一种标志。
3
北京土话又碎又贫,因为语言里的虚词太多了。
比如叠字:磨磨蹭蹭、乌乌涂涂(tū)、邋邋遢遢、马马虎虎(hū)。
比如嵌字:糊噜巴涂(tū)、慌里慌张、噁啦巴心、醋啦巴心。
前加修饰字:如稀里糊涂(tū)、七个不依八个不饶。
后加修饰字:如傻啦吧唧、灰不溜秋、面咕嘟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