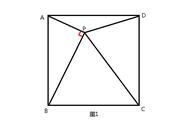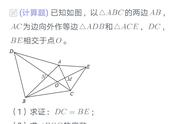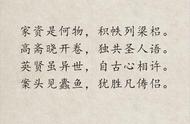皮日休后期创作以记游、咏物、咏史以及咏怀诗为主,题材内敛,情调闲适而略显哀伤。皮诗显示了一些“新变”,但幅度不大,终未形成鲜明的风格。性情贫乏、雕琢过甚使得皮诗少有深厚的意境,创作主体心态的失衡是造成这种失误的重要原因。
晚唐著名诗人皮日休的创作,以咸通八年(867年)中进士为界,明显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以自编行卷集《文薮》为代表,后期的绝大部分作品收录于《松陵集》。由于《文薮》被誉为晚唐“一塌糊涂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所以引发了不少研究者的兴趣,他们对《文薮》的阐释相当深入,可谓胜义迭出。然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其后期创作的研究却罕有问津者。基于欲“知人论世”必“顾及全面”的原则,为达到较为深刻、准确考察皮氏创作状况的目的,笔者不揣浅陋,对其后期创作之显著特征略作阐述,聊为引玉之用。
一
与前期主要在散文领域里驰骋不同,后期的皮日休几乎以一个纯粹的诗人身份出现。其诗作之绝大部分收录于《松陵集》,《全唐诗》中皮氏作品即以此为主干加上《文薮》中的一卷编纂而成。《全唐诗补编》辑得佚诗九首,不过未必都是后期所作。又,《全唐文》收散文七篇,其中《题同官县壁》、《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续酒具诗序》三篇已被今代学者确证为伪作。所剩四篇,《松陵集序》和《破山龙堂记》显为后期作品,而《狄梁公祠碑》与《襄州孔子庙学记》,根据作者行踪推测,则大致可断定为前期所作。有鉴于此,主要通过《松陵集》来考察皮日休后期创作状况便顺理成章了。
《松陵集》编于咸通十年或稍后,由陆龟蒙结集,皮日休作序。此为一部酬唱集,主要收录了皮陆吴中唱和的诗歌。此外,参与其中的还有苏州刺史崔璞以及张贲、郑壁等一批幕府文人和秀才学士。
就题材大致而论,皮日休后期诗作可分为记游诗、咏物诗、咏怀诗、咏史诗四类。
(一)记游诗
皮日休一脚踏进吴中,其壮游南北的阶段也随之结束。以后的几年里,他再也走不出太湖流域。鞍马暂歇可以抚平一颗曾经浮躁的功名心,却难以改变游玩山水以适其志的情怀。皮氏纯粹的记游诗虽不多,但却很有特点。
其中尤以《太湖诗》、《奉和鲁望四明山九题》两组诗为著。《太湖诗》二十章以行踪为线索,所记“皆图籍称为灵异者”。作者笔下景物皆瘦劲怪奇,到处可见的是蛇盘蚓腾、黑穴怪潭等景象,这与“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典型忘世之境是大异其趣的。《奉和鲁望四明山九题》同样描绘了梦中仙境,但全然不见《太湖诗》中那样要么喧闹嘈杂,要么幽僻冷峭的景象,相反历历可见的是一幅幅宁静怡人的仙乐图。这不是万方多难社会的真实写照,而是心中桃源的酣畅抒写。由一个愤世嫉俗的狂者到一个和光同尘的隐者,皮日休的心路历程是痛苦曲折的。
入吴后的皮日休志在禅院道山,这使得记游诗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出尘思想。他对社会似乎渐失热情,“争得草堂归卧去,共君同作太常斋”,类此感叹《松陵集》中俯拾皆是。他陶醉于世外之交的乐趣,且看《访寂上人不遇》:
何处寻云暂废禅,客来还寄草堂眠。桂寒自落翻经案,石冷空消洗钵泉。炉里尚飘残玉篆,龛中仍锁小金仙。须将二百谶回去,待得支公恐隔峰。
寻隐者不遇,本该是多少有些失望,然皮氏却置心平易,仿若兴尽而返。英风敛抑,尽在无言,和后期耽溺佛典一样,皮日休的那些多及方外的记游诗,亦不过是心志的寄托而已。
(二)咏物诗
凡诗主要歌咏实在个体事物的,大体均可入“咏物诗”之流。咏物诗力求体物、状物,写物之情和尽物之态,因而它既可客观描写,又可有感而发。笔者粗略统计,皮日休咏物诗近九十首,几占其后期诗作的三分之一。它在题材上的两个特点是显而易见的:一是所咏之物皆闲静,正与心境契合;二是咏物范围并不宽广,一个院落几乎便可容纳笔底之物。
诗作在构思上暗藏层次,体现出多彩风貌,这是皮氏咏物诗在艺术上的显著特色。有纯粹状物写貌的,如咏渔具、茶具、酒具之诗。此类仅是传达物具之形用,了无深意。有形神俱传的,如《樱桃花》云:“婀娜枝香拂酒壶,向阳疑是不融酥。晚来嵬峨浑如醉,惟有春风独自扶”,图形摄貌,花之风流神采呼之欲出。有托物寄意的,“意犹帅也……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可见咏物若能着“意”一层,则诗格自高。如《咏蟹》云:“未游沧海早知名,有骨还从肉上生。莫道无心畏雷电,海龙王处也横行”。此可视为自况之作,表现了虽蛰居一隅却能自固操守的高洁情怀,透露出等待时机驰骋其志的愿望。又如《金钱花》曰:“阴阳为炭地为炉,铸出金钱不用模。莫向人间逞颜色,不知还解济贫无?”笔调幽默冷隽,对那些好看却不中用甚而不自知的人实在是绝妙的一刺。
(三)咏史诗
咏史对象要么是史事人物,要么是历史遗迹,皮日休的兴趣在于后者。他的咏史诗虽不多,但不乏奇思佳构,其中尤以《馆娃宫怀古五绝》和《汴河怀古二首》出众。
和同代许多作家一样,皮日休亦酷爱“翻案”。长期以来,正统观念都把西施美色惑主看成是吴王身死国灭的主要原因。这种“红颜祸水”的历史观在晚唐遭到了质疑,为西施鸣不平的诗作应运而生。罗隐《西施》一问深刻有力:“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陆龟蒙《吴宫怀古》更是一针见血:“吴王事事须亡国,未必西施胜六宫”。罗、陆的抗议在皮日休这里得到回响。《馆娃宫怀古五绝》其一即云:“越王大有堪羞处,只把西施赚得吴”,一反卧薪尝胆的正面形象,还越王阴毒无能之面目;其二即言越王志得意满之傲慢举止;其三感叹吴王死得狼狈而不自知;其四假设伍员不死,吴王恐怕与西施还在携手同游;其五则云富贵风流云散,当年美人安在哉?“不知水葬今何处,溪月弯弯欲笑颦”,结尾一切归于平静,但似乎又有缕缕怅惘飘然而出。组诗为凭吊感怀之作,字里行间枨触深长,对作为牺牲品的弱女子倾注了无限同情。《汴河怀古二首》中,则以精警的议论见长。在此皮氏又与“尽道隋亡为此河”的传统看法相左,极力赞扬了隋炀帝开凿运河的功绩:“至今千里赖通波”。暴君暴毙实为穷奢极欲的品性使然,为此抹*这一“共禹论功不较多”的壮举是不公平的。在“一荣俱荣,一毁俱毁”观念流行的传统社会里,皮氏此论可谓石破天惊。
千古兴亡悠悠事。历史的厚重和深邃常常击打着气质敏感者的心扉,多少人因此怆然泪下!然而,对于时光移来的变化,皮日休却冷静得出奇。前述《馆娃宫怀古五绝》中,触及到繁华与干戈的场面,君王得意与仓惶的错位,美人作为工具直至香消玉殒的悲剧,可是诗人并未表现出沁人心骨的伤感。
所有沧桑都消失在结尾那幅艺术图景之中,宁静悠长,仿佛历史的水面未曾被吹皱过。在一事同咏的七律《馆娃宫怀古》中,诗人对于艳骨成土、香径泥销的如烟往事亦视之泰然。尾联云“姑苏麇鹿真闲事,须为当时一怆怀”,这与其说是悲怆的感怀,不如说是对无常的参透。将个人的心境托史事以出之,皮日休很好地继承了“咏史即咏怀”的传统。
(四)咏怀诗
诗言志,凡诗都有些咏怀的色彩。之所以独立出来作为一类题材,原因在于咏怀诗均是以“我”为视角,以“我”之生活及情感为中心来构织诗篇的。隐士情怀借助于生活化的感受来显现,这是皮日休咏怀诗的突出特点。
皮氏随缘自适,所遇皆安,文士兼隐士的生活使他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桂静似逢青眼客,松闲如见绿毛翁”、“茅山顶上携书簏,笠泽心中漾酒船”……类似陶然自乐的抒写,在《松陵集》中随处可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皮氏用大量的笔墨记录了与陆龟蒙的友谊,人情味绵厚深长。“顾余客兹地,薄我皆为伧。唯有陆夫子,尽力提客卿。……敲门若我访,倒屣欣逢迎”,他乡遇知音,感念于心,珍藏于怀,多余的言语反而苍白无力,迎来送往间,尽显人生真趣。“既见陆夫子,驽心却伏厩。……唯恐别仙才,涟涟涕襟袖”,因仰慕高风到志同道合,情好又恐销魂别,相得之欢,复夫何言!抒情的生活化导致了感受的个性化,一蔬相赠、半鱼之馈、一壶留饮……皮日休的诗笔伸向了交往的每一个细节,索然无味的生活在友谊的映射下生机勃发。
疾病和贫困与皮氏形影不离,他也时时赋之篇章。痛苦与人生相伴,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但他却想淡化或刻意忘记痛苦,哪怕求得心灵的片刻安宁。女儿早夭是此时最为伤心的事了,然而他在咏悼时用语总能与克制的心情一致。《伤小女》云:“一岁犹未满,九泉何太深。唯余卷书草,相对共伤心”。起两句感情激越几不可自持,后两句则马上平抑,犹如化嚎啕大哭为低首啜泣。元稹亦有类似之作,其《哭子十首》之五云:“节量梨粟愁生疾,教示诗书望早成。鞭扑较多怜校少,又缘遗恨哭三声。”诗以细节回忆更显难堪之情,诗人愈写愈沉痛,以致纵声大哭,感情一任奔越而不加阻滞。两相比较,“理性”和激情判然有别,性情面貌泾渭分明。
综上所述,皮日休后期诗作在题材上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内敛。他把表现的范围从国计民生转到了自己的心里身边,开始了作为隐士的吟唱生活。他用诗歌来娱情酬答,写作日益个人化。他对曾经倾注过政治理想和热情的社会表现得十分淡漠,给人近乎麻木的印象。人生消尽大喜大悲,所为不过在平常的生活中觅得世俗的乐趣,这既是遣尽光阴的手段,也是壮志难举的心理代偿。因而,其诗歌情调是一种忧郁的闲适,让人感受到时代某种回光返照式的“平静”氛围。
二
平观皮日休时代,诗坛以“两极分化”为突出特点。一极是以韩俚、吴融为主将的艳体诗派,所作多是“裙裾脂粉之诗”,号为“香奁体”。诗作反映了上层阶级精神失路、心理没落的状况。诗艺上取法齐梁,杂以温、李,刻画精细,绮丽错杂。另一极则以杜荀鹤、聂夷中、罗隐等为代表,可称之为穷吟诗派。此派诗人出身草泽,穷饿无聊,他们把表现苦难现实作为诗之主题,极力张扬儒家功利主义诗风。这派诗人多愤世嫉俗,下笔甚至“如戟手交骂”。艺术上则多用讽刺手法,语言通俗晓畅,然亦时常失之浅露。
应当说皮日休前期创作正可与穷吟诗人惺惺相惜,但后期则与之渐行渐远,直至分道扬镳。变化若此,仅从诗艺角度观察,这未尝不是穷力追新的结果。皮日休认为才如天地之气,变幻无常,故“才之用也,广之为沧溟,细之为沟窦;高之为山岳,碎之为瓦砾;美之为西子,恶之为敦洽;壮之为武贲,弱之为处女。大则八荒之外不可穷,小则一毫之末不可见”。此无疑是一种通达的发展观,表明他对才性变化所形成的各种风格都持欣赏态度。在这种通变和包容观念支配下,皮日休开始了创作的转型。他既鄙弃艳体的轻浮,又不满穷吟诗派的“俗”气,他试图另走新路。
皮诗在题材上的选择,与同时代诗人其实并无大异,亦不过是“唯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不过即使如此,皮氏开拓新题材的意识还是相当自觉。最突出的一点便是,他热衷于“查缺补漏”并形诸歌咏。比如他在和作了陆龟蒙十五首《渔具诗》之后,意犹未尽,又作《添渔具诗》五首“用以补遗者”,并因“渔家生具,获足于吾属之文也”颇为自得。《酒中杂咏》有感于古今茶歌虽多,然“其具不形于诗”,因此欣然歌之咏之以补前人不到者。
晚唐“气弱格卑”,在体裁上罕有多面作手,比如杜荀鹤一生专攻近体,聂夷中只擅乐府和五言等。皮日休则表现出兼容的气势,于众体无所不施。除古体、近体外,他还好作回文、叠韵、离合、四声等杂体。晚唐古诗习者虽多,然篇数锐减,不及中唐的四分之一。皮日休是古诗作得较多的一位,约有四十首,而且动辄五百言、三十韵,称得上鸿篇巨制。众体兼备,而又多作古体,皮诗体裁上的求全和复古倾向,多少有些“新人耳目”。
在语言风格上,皮日休力求多样化。他主要走了两条路子,一路追求清新流丽,一路经营奥博险涩。前者恰与“绮罗香泽”反照,后者则同“俚俗浅切”异趣。从题材上看,咏物、咏怀诗,语言多清丽一些,而记游诗则侧重于奥涩;以体裁观之,则其绝句最为清丽,而古体则多是奥涩。
平心而论,皮诗“新变”的步伐并不大,效果亦不显著。题材上要做到无事无意不入诗,非大手笔不能为。仅以“补缺”的方式来扩大歌咏范围,不免弄巧成拙,反见诗道之日暮途穷。体裁上虽能面面俱到,但要在艺术上也达到均衡状态,于皮日休而言怕是心余力拙。前人指责他“律体刻画堆垛,讽之无音”,一些杂体诗“俱无意味”,确实是切中肯綮的。尽管晚唐诗家“务以精意相高”,一个个绞尽脑汁想不随人踵,但是想要在很大程度上跳出窠臼是不现实的。就皮日休论,骨子里同样与上述两派有融通会意之处。形式上讲究工整,语句上狠命锤炼,这是晚唐诗的共性之一,即使是目为“俚俗”的穷吟一派,雕琢也甚于以前。皮日休不同之处显著表现为偶作拗体、押险韵,尚奇求怪,借牛鬼蛇神来引人注目;他追崇清新流丽,实质上与穷吟诗人以“自然”相标榜并无大异,他的新处在于把口语“粗鄙”的特征去掉,使之妥帖平易。再从纵的方面观察,于本朝人物他景慕的是孟浩然、李白、白居易、韩愈、李贺等,皮诗中清新流丽的一路恰与李、孟、白在质性上相通;另一路则是怪韩鬼李一派逞奇斗险的继续。人说“皮诗中多宋调”,所谓“宋调”,主要指议论、才学、散文化特征,而这些早在被江西诗派奉为鼻祖的老杜集中屡见不鲜。后经韩愈、孟郊诸人大畅其道,实际上宋诗法门已经开启,皮诗充其量不过唐诗“宋调”余响而已。
由此可见,皮日休诗歌风格特征的形成主要建立在历史继承和世风融通的基础上,其创新求变的
幅度并不大,个人面貌要仔细辨认方能呈现。叶燮在《原诗》中肯定了其“自领一队”的求新精神,并把他与“卓然自命”的古今作者相提并论,然而叶氏也不得不指出其“甘作偏裨”的事实,这正是皮诗风格不得特立迥出的主要原因。
“甘作偏裨”先输入志气,与“卓然自命”并论岂不自相矛盾?与其说皮日休“自领一队”是出于自愿,不如说是无奈。他对当时情势了然于胸,感慨道:“由汉及唐,诗之道尽矣。吾又不知千祀之后,诗之道止于斯而已,即后有变,而作者余不得以知之”。面前横亘的高峰难以逾越,他对将来有所期待,但充其量不过是谨慎的乐观罢了。不敢与前人较长论短,宁弃传统题材开掘扩张之特征而代之以内敛收缩,这种自卑的心理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艺术上的失误。
三
皮诗最大的失误在于缺乏深厚的意境。所谓意境,乃性情与物象交融浑成的境界。形象与情韵相生相合,是意境的本质要求。
性情的贫乏是意境不深厚的首要原因。皮日休似乎要刻意“忘记天下”,因而极力克制激情,闲适中近乎冷漠。很难想象,这种心境下的文字会达到多高的境界。且看他的《夏初访鲁望偶题小斋》:
半里芳阴到陆家,藜床相劝饭胡麻。林问度宿抛棋局,壁上经旬持钓车。野客病时分竹米,邻翁斋日乞藤花。踟蹰未放闲人去,半岸纱绡待月华。
诗用白描手法写了自己从白天直至月出专访陆家的情景,性情很是平淡闲适,除微微透露出些许喜爱,见不出灵台有何风吹草动。不妨和同类题材略作比较,请看孟浩然《过故人庄》: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同样写一次相访,孟氏并不全写景,而是参之以日常场面描写,溢出一股不可抗拒的亲和力。这里人境融合,诗人淳厚、俊朗、乐观之性情斑斑可见。孟氏是一个“人世”很深的隐士,皮氏却恰恰相反。正是性情使然,孟诗虽“信口道出”,但“浅之至而深,淡之至而浓,老之至而媚。火候至此,并烹炼之迹亦俱化矣”。皮诗则除“浅”“淡”之外,鲜有远韵,人仿佛在诗外冷眼旁观,离浑融境界尚有距离。
性情的淡泊乃至冷漠必然使创作失去持久的动力,从而难免不会落入第二义——向外乞灵于技法。皮氏古诗“另开僻涩一体”,斧凿痕迹明显。首先,他大量以赋法入诗,铺张扬厉,唯恐言之不尽。如《吴中苦雨,因书一百韵寄鲁望》,先言雨前征兆,写乌云变化之奇特,状水底生物之狂躁;次叙狂雨下泻之情景;复言及自己雨中受困的狼狈境地;转而推己及人,遥想陆龟蒙困窘之状,继而写彼此交往的情形,赞其穷不改道的节操,最后以宽慰对方作结。此从章法上看,与散文何异之有?此等铺排固然酣畅淋漓,但诗味也不觉自损三分。前人指出:“陆龟蒙、皮日休知用实,而不知运实之妙,所以短也”,确为的评。又好罗列典故,避熟就生,逞才炫学,如与陆龟蒙的两篇五百言唱和,简直就是矜夸学问的比赛。“作诗文有意逞博,便非佳处。犹主人勉强遍处请生客,客虽满座,主人无自在受用处”,此语若用来批评皮陆此种习气,倒是恰如其分。
其次,议论过多损害了诗中形象的完整。恰到好处的议论有如画龙点睛,能使意境得到升华。但以诗作论,乃至议论游离于形象之外,终会破坏意境的完整性。皮日休擅文好论,因而把散文的笔法和议论的习惯带进了诗中。夸张一点说,皮日休无诗不论。他的古体诗,议论的成份几与描写相当,如《奉和鲁望阴符经见寄》等篇。他总喜欢在刻画之后,于结尾处“显其志”,而且有时话说得太尽,反倒平添“蛇足”之憾。
再次,皮日休炼字求句有时太过,造成“有句无篇”的现象。唐末风气,诗人每以佳句相高,风会所及,皮陆酬唱除出“新意”外,还以“俊句”相赏。王夫之《唐诗评选》云:“皮、陆松陵唱和诗奕奕自别,巧心佳句,诚不可掩”,《载酒园诗话又编》列出皮日休十一联“俊句”,以为“较陆诗更觉醒目”。一味求巧句,主观上即容易放弃对全诗意境的追求,理想中和谐浑成的意境也就难以镕铸。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理所当然要遭受批评,《薑斋诗话》毫不客气指出:“若但求于句巧,则性情为外荡,生意索然矣。松陵体,永堕小乘者,以无句不巧者也”。不单皮、陆,同时代诗人几乎都醉心于这种在细功夫中显才华的手段,在争一句之巧、一联之奇上耗费了太多的才智和精力。这和盛唐作风简直背道而驰:“盖盛唐人一字一句之奇,皆从全首元气中苞孕而出,全首浑老生动,则句句浑老生动,故虽有奇句,不碍自然。若晚唐气卑格弱,神韵又促,即取盛唐人语入其集中,但见斧凿痕,无复前人浑老生动之妙矣”。
意境的缺少和雕琢之盛行,预示着皮日休及同仁走上了唐诗发展的末路。“唐祚至此,气脉浸微,士生斯时,无他事业,精神伎俩,悉见于诗”,社会没有给诗人太多实现自我的机会,“弃儿”般的感觉带来无限失落。牢*满腹也罢,怨天尤人也罢,最终还是要把心灵抚平,于是他们找到了作诗的手段。手段习用,渐成目的,人生价值藉此肯定,这就不可避免地迫使他们为作诗而作诗。再也没有什么比成为一名诗人更重要的了,这一沉重的精神负担又怎能不让人诚惶诚恐?诗国过去的辉煌只能望洋兴叹,皮日休他们深感要更上层楼便有如循蜀道而登青天了。但问题恰恰在于,“喜新厌旧”是艺术的本能,创造总是生命深层中不可阻遏的愿望。为了尽力发出声音,他们不得不“新其小智小慧”,把诗引入精雕细琢一途。一旦“新变”念头过于执着,即有“无限诗魔,入其胸中”,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其必欲胜前辈者,乃不及前辈耳”,事实也正是如此:他们企图另辟蹊径,走不多远,发现又是步人后尘;他们刻意搜奇抉异,务精弄巧,最终依然遭到“千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终”的讥评。诗歌发展自有其内在和外在的规律,诗人只有因势利导,才能促成艺术上的本质飞跃。在不具备新变的条件下,诗人企图仅凭有限的才华为穷途别开天地,勉为其难便是意料中的事了。
“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生活毕竟是诗歌创作的源头活水,它不仅提供“诗料”,而且涵养性情。某种程度上,诗境即人境,换言之,意境的高低和性情的丰富与否密不可分。为作诗而作诗,舍弃的恰恰是诗的真髓,诗最可宝贵的气象和风骨往往就是在“作”中丧失殆尽的。明了这个近乎常识的道理,对包括皮日休在内的晚唐诗人虽求“新变”但终未振起的原因便“思过半”了。(彭庭松)
欢迎加入善本古籍学习交流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