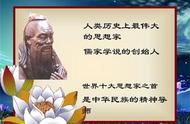莱布尼茨(右图)、伏尔泰(左图)等借孔子的人道主义抨击欧洲世袭贵族统治
17世纪,西方天主教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与孔子学说不期而遇。他们是第一批将孔子这个“东方智者”相对全面地介绍给西方的人。当时,西方启蒙思想家们包括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等都为孔子的人道主义而感到振奋,并以此为武器来抨击欧洲的世袭贵族统治。使莱布尼茨感到特别惊异的是,他所发明的二进制运算,早已存在于中国古老的《易经》里。在《易经》里,阴爻和阳爻可以分别代表“0”和“1”。他兴奋地写道:“这说明,古代的中国人和当代人相比,绝对是超前的。这不仅仅体现在孝道(这是最完美形态的道德的基石),还体现在自然科学方面。”(Cook &Rosemont,1994)
19世纪国门遭受凌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破碎

鸦片战争之后一群儒家官员,特别是林则徐(左图)和张之洞(右图),发起了“自强运动”
直到19世纪,中国才真正地感受到西方的冲击,并开始视西方为儒家传统的强劲对手。19世纪欧洲的来访者总体上完全漠视中国人的感情和价值。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他们不断地发起军事袭击,用武力迫使中国接受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开放口岸、在中国建立租界地。
这些严酷的现实迫使中国人反思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一群儒家官员,特别是林则徐(1785—1850)和张之洞(1837—1909),发起了“自强运动”,他们试图以中国传统为“体”、西方文明为“用”:“中学为体”,是强调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社会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是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效仿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武备、律例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 ,举办洋务新政,以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但是事实上根本无法毫发无损地将儒家传统作为一个优越的“体”来保存,而仅仅傲慢地、有选择地接受某些西方学说为其所“用”。
“打倒孔家店”后,马克思主义成主流,刘少奇以儒家术语谈“修养”

刘少奇写下了虽然简短但影响极大的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20世纪之初,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自秦始皇以来声势最为浩大的反儒浪潮。儒教被批为中国万恶之根源。高喊着“打倒孔家店!”“欢迎德(Democracy民主)先生和赛(Science科学)先生!”这些口号,一群从中国文化遗产中挣脱出来的学者,如陈独秀(1879—1942)、蔡元培(1868—1940)、李大钊(1889—1927)、鲁迅和胡适(1891—1962)等,领导了一场全盘反对儒家传统文化的运动。这些知识分子还将大量西方启蒙思想介绍到中国,包括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穆勒(John S.Mill)的《自由论》、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尼采的“超人”观念、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卡尔·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以及杜威的实用主义。
1949年,共产党领导成立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成了主流的意识形态。中国以外的许多人不知道的一件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59年至1968年间的*刘少奇(1898—1969),写下了一本虽然简短但影响极大的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这本书里,刘少奇不仅引用了儒家的术语“自我修养”,还多次引用了孔子和孟子的话,用以说明,自我修养是一个要经历持久艰难困苦的转化过程。
“儒学第三期”,成为开解后现代主义世界难题的丰富哲学资源

美国汉学家列文森写就《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著作,影响深远
1976年,中国人开始重新评价*思想,并开始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一本题为《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e:A Trilogy)的书里,美国汉学家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写道:“最初,他们(儒家)的观念是一种能量,是一个鲜活的社会的产物和知识的财富。最终,当产生它和需要它的社会渐渐开始化解,它变成了一个影子,仅仅存活在许多人的心中,并且只是作为它自身而被欣赏…… 儒家人物一贯看重历史,而现在他们自己变成了历史。”
列文森还没有意识到,被牟宗三等人称为“儒学第三期”的时代已经来临。西方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暴露出来的许多日益深化的危机,与一直保持儒家传统的“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成功形成了对比,触发了对西方知识传统的批判性的反思以及对儒家思想的关注。通过对儒家思想的现代化的阐释,当代儒家学者越来越确信,儒家思想蕴含了开解后现代主义世界难题的丰富的哲学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