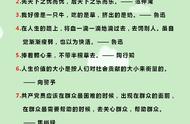39岁时,他的思想有了更大的变化。他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从一个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依附门阀大地主政权转变为坚决不合作。思想上也曾有“贫富常交战”的矛盾斗争,但结果总是“道胜无戚颜”,宁肯潦倒终生,也决不妥协。
陶渊明深知“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的人生规律,可又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于是只有委屈自己,做一个有志有节而穷困潦倒的平民百姓。“种豆南山下”,“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

辞官归园的生活开始是游哉悠哉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归园田居》)。这一切真是“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
然而,好景不长,诗人44岁以后,遇到一系列的不幸,住宅两次失火,田地多年逢灾,妻死女夭,家境日趋萧条,已经走上了“居无仆妾”,甚至断炊、乞食这种山穷水尽的悲惨境地。生活巨变直接影响他的创作,田园诗的情调、色彩发生了变化,明朗、恬静的画面渐为晦暗、凋敝的图景所替代。

“阡陌不移时,邑屋或时非。履历周故居,邻老罕复遗”(《还旧居》);“荒途无归人,时时见废墟”(《和刘柴桑》),后期诗不同程度揭示了当时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悲惨遭遇,真实地反映了东晋时代的阶级矛盾。
早年那位“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翘首冥思的诗人已被贫困折磨得失去了浪漫的情趣,空有满腹诗文却不得不遭受饥饿之苦,空有济世之志却不得不蜗居穷乡僻壤,潦倒终生。

陶渊明出仕达五次之多,笔者一直有种看法:这是他的性格造成的。他社交能力差,连最起码的人际交往都无法应酬;他出类拔萃,其非凡的才能令众人嫉妒,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他超凡脱俗,不把大众看在眼里,常常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合作精神不够……他自己也很敏感,又很在意别人的看法,于是很渴望逃离世俗,乡村便成了他假想的安乐窝。
他的这种性格的形成,社会动荡不安是一个因素,“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用人制度是一个因素,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黑暗官场是一个因素,但更多的是自己的性格因素——精神的高尚造就他性格的孤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