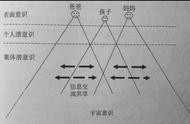郁达夫(左一),现代作家,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
-
郁达夫的回信直接而「不留情面」:
「像你这样一个白脸长身,一无依靠的文学青年,即使将面包和泪吃,勤勤恳恳的在大学窗下住它五六年,难道你拿毕业文凭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会下起珍珠白米的雨来的么?」
好在,命运的指向总是峰回路转——收到郁达夫的回信不久后,沈从文的文章终于首次在《晨报副刊》获得发表。
这是一个令人雄心勃发的开始。昔日的无名小卒,终于一只脚踏进了他梦寐以求的京城文人圈。
初试啼声的沈从文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彼时的他还不能想象,他的出现,将彻底改写中国现代文学史。
02最后一个浪漫派:关于爱的「信者得救」
在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的评比中,沈从文中篇小说《边城》位列第二,仅次于鲁迅的《呐喊》。

《边城》改编同名电影
-
对生活在都市的中国人而言,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我们对田园牧歌式乡土生活的最初想象。很多读者说,之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忍不住重读《边城》,是因为,这部小说能够给予读者一种由心而生的「相信」——相信人性中有真正的洁净、纯良,相信美好的情感是生而为人最应当珍重的东西。毋庸讳言,在以痛斥黑暗、控诉不公为主流的20世纪文学浪潮中,沈从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类」。「沈从文写的小说材料很新鲜,就像乡下拿来的水果没有经过加工,跟左翼反映农村苦难、阶级斗争的小说,包括鲁迅等人的乡土小说都不一样。」

凤凰的沈从文故居(于楚众 摄)
-
显然,十四岁参军、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并非是「不知人间疾苦」或有意回避——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他的文学理想是建造一座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他希望借助文学呈现一种更普世、更深广的人性诗意。一种不同国家民族间共通的,对「美」和「真情」的呼召。这也正是沈从文作品的伟大之处。「我赞美故乡的河,正因为它同都市相隔绝,一切极朴野,一切不普遍化,生活形式生活态度皆有点原人意味。」
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回忆道,沈从文「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美”的爱好者,对于由于人的劳动而创造出来的一切美的东西具有一种宗教徒式的狂热。对于美,他永远不缺乏一个年轻的情人那样的惊喜与崇拜……」

1961年,汪曾祺(左)与老师沈从文在中山公园
-
和那些「有两副面孔」的作家不同,沈从文是一位真正相信,并践行自我文学理想的写作者。换言之,他用自己的人生论证了「人性美」与「浪漫派」的可能性。一个最有力的例子,便是他与张兆和的爱情。 他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他说:「我们相爱一生,一生太短。」
后人在沈从文异地写给妻子的信中,读到了他的真挚和柔情蜜意:
「我就这样一面看水一面想你。」「三三(沈从文对张兆和的爱称),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想到你。」 「我不为车子所苦,不为寒冷所苦,不为饮食马虎所苦,可是想你可太苦了。」 「但一个人心中倘若有个爱人,心中暖得很,全身就冻得结冰也不碍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