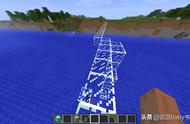2023年伊始,雨果的生活开始加速。他接连被各路媒体、电视报道、拍摄,作为嘉宾上了综艺。
他乐于接受这些,至少已经熟稔流程。接到我们采访邀约时,他先问了是否要拍摄,又再确认了“咱们这个也是义务的是吧”。
但媒体一个接一个地来,他有些难对付,干脆出去骑了一个月山地车,从满归骑到海拉尔。回来后又被邀请进根河市政协开会,“穿着西装人模狗样的”。
五月底,他把六头驯鹿拉到景区,在呼伦贝尔景区的撒欢牧场,按门票分成。驯鹿旅游已经火了几年,因为心疼鹿,雨果家几乎是牧民中最晚开始驯鹿生意的。
驯鹿在森林里受伤,吃点草药就能好。但在人类世界里,它们总是无法适应。20年前,被没收猎枪的鄂温克人和驯鹿一起迁下山。在敖乡,被圈养的驯鹿“死伤惨重”。在政府的默许下,酋长玛丽亚·索又带着一部分族人和鹿回到森林里。维加说,是驯鹿救了鄂温克人。
在景区,游客会成为宠物病毒的宿主,传染给驯鹿。雨果家的驯鹿被病毒传染后开始尿血。在山上的柳霞心疼鹿遭罪,一个劲托人打听鹿怎么样了。
这次假期去哈尔滨旅游时,雨果看见山上的驯鹿待在松花江旁,附近在“咣咣放音乐”。而驯鹿通常在白天休息,纷至沓来的游客扰乱了它们的生物钟。雨果庆幸冬天没有把驯鹿拉去做文旅。
外面的世界变化得太快了,新的社交媒体颠覆了鄂温克人刚刚适应的现实,他们发现,“拉驯鹿去旅游景点几个月,到兜里的钱有10来万”,但雨果觉得这钱拿得不踏实,“真的是不开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驯鹿是外人认识他的标签,也是他无法抹去的自我认同,但这能用来换取金钱吗?雨果没想明白。已经成为文旅规划路线的家,到底是眷恋的故土,还是仅仅给外来游客带去休憩想象的景观?他也没想明白,只是不开心。
和雨果见面后,摄影师猫发现,昔日的男孩已经完全独立,知道怎么去打理生意,在妈妈去世前已经把驯鹿点支撑起来。“他不再有任何牵挂,因为就剩他自己了”。
他觉得,即使一个人非常自傲,不用鹿赚钱,让鹿自然地生活在森林里,保留它们,尊重它们,最后总有人会把他们替代掉。鄂温克的鹿越养越少了,山上只剩14户,汉民逐渐替代他们成为养鹿的好手。雨果只能尽量尊重驯鹿,同时为自己找生存的余地。

在山上的四年里,他也劝过母亲把驯鹿卖掉,跟他下山,“一卖也是两百多万在手,你也是百万富翁”,但柳霞舍不得她的鹿,驯鹿就是他的家人,“酒我是能戒,但鹿我是一个不带卖掉的。”
和上一代人相比,雨果身上已经没有狩猎文化的印记。可比起下一代,八岁之前的雨果至少还经历过骑驯鹿搬家,用枪打猎、生吃动物心脏的日子。一位在大兴安岭生活的汉族青年说,他基本没见过还保留原来生活习惯的鄂温克人,进城定居或在民族乡的,要么成为林业工人,要么进入体制内,“小时候有很多鄂温克的同学,除了长相有点不一样,没感觉有啥不一样”,跟他差不多大的基本都不会说自己的语言了。
那么新一代的使鹿鄂温克人,还有可能坚守自己的文化吗?
顾桃的回答是,只能是一种惋惜,更准确的说法是,最后的挽歌。他记得,拍摄《犴达罕》时,维加有时候在篝火边一动不动待两三个小时,“看火里死去的猎人”。在影片的结尾,黑白色调的维加走在白雪皑皑的路上,说:“现在社会进步了,那我得背着点手。狩猎文化,消失了,工业文明带来一个悲惨的世界。如果有更文明世界的警察向我开枪,那就开枪吧。”
他的鄂温克外甥雨果用一种更年轻的方式诉说,他创作了一段Rap:
一个萨满的家族 在退出历史舞台
多么悲哀请求上天宽待一定不要懈怠
离开森林要重谋生路看不见温暖铁炉
吃完列巴喝完茶翻山越岭找鹿的日子
从背枪驰骋林海
到家住隔壁临海
他付出全部真心
也渴望能受尊重
桦树皮船飘进博物馆使他从此灰心
他只在绘画世界里面能够得到一丝关心
每日家中街头酒瓶满地醉生梦死
他不想成为现代社会手中的一颗棋子
凌晨3点走在无人街道打开画纸
消失的文化冰川的融化都令人发指

2024年2月初,雨果结束了旅行,坐着火车从哈尔滨回到海拉尔。他本想接着去趟日本,但想到这是柳霞过世后的第一个春节,他应该回家给母亲倒杯酒,再点上长明灯。
除夕夜,这天雨果一个人待在木屋里,听着鞭炮声,有些失落。山上听不到声响,但在那总会想起母亲。
山下的居民点被翻新过两次,已经从千篇一律的红顶白房变成了深咖啡的北欧风木屋,木屋上挂上彩灯,也铺满了现代的痕迹:满目的民宿和在卖鹿茸和各种鹿角制品特产店。
往常,他会和群里的三百多位粉丝互动,或是干脆直播,但今天他也不想开了。他发视频说,希望粉丝在除夕夜多陪陪家人。
村里人知道今年他只有一个人,喊他来家里吃饭,但他觉得自己会打扰其他人团圆,决定哪也不去,随便做点吃的上床睡觉。这么多年,他跟柳霞在山上已经习惯了“不那么热闹地过”,他们不讲究这个,过年煮盘饺子,柳霞喝多了就睡觉。
今年4月,雨果打算去西藏,成为第一个骑山地车到拉萨的鄂温克青年。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愿望。
但那是生小鹿的季节,鄂温克最忙的时候。驯鹿怎么办?
因为“前段时间驯鹿在哈尔滨中央大街溜达一圈升值了”,从四五万一头涨到六七万。而20年前,顾桃刚开始拿DV拍摄时,一头驯鹿也就3000、5000元。雨果动了将驯鹿卖掉的念头。“四十多头鹿卖了,200多万……”他想用这笔钱去北美(可能是阿拉斯加)学电影,也学他们养驯鹿的方法,再给全世界养驯鹿的民族拍一个纪录片,名字想好了,就叫《驯鹿之地》。
可就在柳霞去世的十天前,他还答应母亲要尽全力照顾驯鹿。
所以他接着说,“不知道,反正有点烦,毕竟是妈妈留下来的。”这个想法一直隐约存在他的脑海里。妈妈走了,没亲没故,这样的念头更强烈了。或许可以卖一部分给同民族的,雨果想,这样驯鹿还能在山上,剩下的留给妹妹继续养。
要走还是要留?至少今年,妹妹会替他饲养驯鹿。姥姥生前送过老孙驯鹿,拜托他照顾柳霞,老孙也会接着协助雨果的妹妹。

*雨果与驯鹿
要走向哪里呢?雨果没想明白,他拍了条视频问网友。一个人的回答让他心安:我们称你为森林之子,当然希望你可以走向森林,但是你作为你自己,可以走向任何你喜欢的地方。
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他想重新拿起镜头表达自己,2015年,他第一次把镜头对准柳霞,拍摄了第一个作品《留霞索罗贡》——柳霞的名字。这支七分半的短片后来被英国的纽卡斯尔大学珍藏。但他自己不太满意,“可能外国人看重内容,觉得这个女人还挺酷的。”
回到森林的四年里,雨果又拍了不少关于柳霞的片段。顾桃鼓励他剪出来,哪怕只是短片。
如今,雨果觉得自己已经过了对Rap“狂热”的阶段了——“没有画面,差点意思”。对他来说,短视频是为了生存,应该有更值得的东西被保留下来。
他算幸运,到过外面的世界,也知道森林的模样,森林的味道始终没有变——桦树的叶香,樟松的松香,还有蚂蚁的酸味。驯鹿踏着过膝的雪跑过,带来的风从脸颊吹过。雨果说,这里的一切和几十年前一模一样,从来没有变过。“变的只是人”。
撰文:Qiu
编辑:刘欣佳
图片承蒙采访对象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