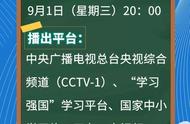沈曾植(1850-1922)清末民初著名的学者、书画家。字子培,号撰斋,别署乙盦等,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
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官至安徽布政司。在学识方面,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精通史学、佛学、边疆地理之学,著有《无秘史笺注》、《蒙古源流笺证》、《乙卯稿》。他以“硕学通儒”蜚振中外,誉称“中国大儒”。1901年任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校长),改革旧貌,成绩卓著。
沈氏书法早精帖学,得笔于包世臣,壮年嗜张裕利;其后由帖入碑,熔南北书流于一炉。在书学上,沈氏首次系统而详尽地阐述了碑与帖的联系发展脉络。在实践上早年攻帖学,仿黄山谷时尚不能得势,中年学钟繇,后来穷魏碑,极章草,终使“抑扬尽致,委曲得宜”,进入了碑帖融合的独有理想境界,创造了奇峭博丽的沈体书法。曾熙曾评价沈的书法:“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处在不稳”。沈氏还善绘山水,但艺术成就不如书法。
沈曾植的书法艺术影响和培育了一代书法家,为书法艺术的复兴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于右任、马一浮、谢无量、吕凤子、王秋湄、罗复堪、王蘧常等一代大师皆受沈书的影响。书法艺术是书法家的自身涵养、文学功底、学问积蓄、学识个性和天赋、气质等贯融的表现。沈曾植作为一名大学问家,他的书法艺术日臻化境。评论家认为:“书法家的字求法;画家的字求趣;学者的字书卷味;碑学书家的字有金石气;帖学书家的字滋润丰腴肌理;唯寐叟翁(沈曾植)全有,故能兼美。

沈曾植《行书包世臣论书两首诗轴》纸本行书
127.8×66.2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释文:中郎派别有锺梁,茂密雄强正雁行,底事千文传祖法,顿敎分隶意参商。
吕望翩仙接《乙瑛》,峻严《孔羡》毓任城,欧、徐倒置滋流弊,具体还应溯巨卿。
款署:复青仁兄属,寐叟。
钤印:知一念即无量劫(朱文)、寐叟(朱文)、海日楼(白文)
同其他朝代一样,清王朝也经历了出盛世到衰世的转变。道咸之间,虽有中兴,但亦隐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同光年间,社会黑暗,吏治腐败,民生凋敝,道德沦丧,学术衰微。鸦片战争的后遗症与西方列强的持续入侵相互夹攻,内忧外患,错综复杂,大一统的局面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这是一个不幸的时代,是一个既杂乱无章又有些散漫自由的时代。
一代书法大家沈曾植就诞生于这样的时代。他的一生经历了戊戊变法、洋务运动、张勋复辟、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历史事件,见证了晚清时期所有凄凉与萧*。他的一生是在国运日衰与世风日下的泥淖中度过的。
一 生平与治学经历
沈曾植(1850—1922年)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别号甚多,有:薏庵、檍盦、乙僧、乙叜、释持、寐翁、睡翁、?香病叟、孺卿、皖伯、宛委使者、菩提坊襄病维摩、梵持、建持、持卿、其翼、随庵、守平居士、谷隐居士、浮游翁、楚翅、东轩、东轩支离叜、灊皤、灊庸、袍遗、东湖盦主、媻者薮长、姚埭老民、紫藟癯轩、癯翁、东畴小隐、逊斋、逊翁、巽斋、遯叟、李乡农、餘斋老人等等。浙江嘉兴人。其祖父沈维鐈,进士出身,官至工部左侍郎,人称“小湖先生”。曾国藩是他的学生,著有《补读书斋遗稿十卷》。曾五任学政,务尚有用之学,一生校刊之书颇多。可惜的是沈曾植八岁时,其沈宗涵逝世,家道衰落。他从小跟母亲诵读唐诗,通音韵之学。虽因家贫,而读书之志,未尝一日废过。在孙春洲、周克生、王楚香、俞幼珊、高儁生、秦皖卿、阮际生、朱厚川、用饬侯、王莘锄、罗吉孙及长兄沈曾棨的指导下,“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见王国维《沈乙尽先生七十寿序》),逐立“修身、治国、平大下 个人产”大志。
沈曾植在《定庐集序》中称:“少孤,独学天友。所由粗识为学门径,近代诸儒经师人师之渊源派别,文字利病得失,多得之武进李申耆及吾乡钱衎石先生文集中。两先生,否私淑师也,而钱先生同乡里为尤亲。”稍长研究史学掌故,潜心于律法与舆地,李慈铭的评价是:“钩贯诸史,参证舆图,辨音定方,具有心得。”(见《越缦堂日记》)他在乡试时.有关舆地的答卷为翁同和所激赏,视为通人。1880年(光绪六年),他考中进士,供职刑部,精研古今律法,著有《汉律辑存》、《晋书刑法志补》等书,薛允升推为律家第一。之后,他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今外交部)章京,主管俄国事务,因而,益究四裔舆地之学,于辽、金、元三史,创获颇多,声名远播。1893年,俄罗斯使臣喀西尼以《唐阙特勤碑》、《突厥苾伽可汗碑》、《九姓回鹊受里登汩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影印本,求沈曾植翻译考证,沈作三碑跋博得众人认同。此事后来广为流传,西方学者也多加以引用。在沈曾植一生的著述中,有关舆地之学占了很重要的部分,计有《元秘史笺注》、《皇元圣武亲征录校注》、《岛夷志略广证》、《蒙古源流笺证》等十余部。

在北京任上,与其弟沈曾桐治珠算,享有盛名。相与交往密切者有文廷式、康有为、袁爽秋、朱一新、陶濬宣、杨守敬、汪康年、梁启超、盛伯熙、黄仲强、徐世昌、王鹏运、袁世凯、’梁鼎芬、邹代钧等。四十岁后,深究焚学,会通儒佛。晚年因经济拮据,在沪上鬻书自给,时间约在1919年前后。《清史稿》称:“曾植为学兼综汉、宋,而尤深于史学掌故。”此说略显简单,其门生王国维曾有过较为客观的总结,兹迻录如下:
“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原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安,拓其区字,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居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钨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见《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因受李申吾与钱衍石的影响,沈曾植做学问向来注重经世致用。时值清末变法,整个社会体制与思想风气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时的“新学”与“旧学”之争是非常激烈的,一些先进人士纷纷向西方寻找真理,其代表人物便是康有为。沈曾植与康有为交往密切,曾为其发动公车上书出谋划策,但在行动、性格上又颇多不合,两人始终是若即若离的关系。沈曾植在思想上比较务实,又兼有儒家学者的风范,主张循序渐进,反对狂飙式的社会变革。值得一提的是沈曾植在1878年结交广东名宿陈澧,1898年入张之洞幕府,执掌武昌两湖书院,这两份经历对他一生祟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张之洞推行洋务运动,善用权术和智慧作折衷新旧之论,沈曾植非常拥护。张对沈亦甚为器重,称沈为“凤麟”,有“平原宾从儒流少,今日天骄识凤麟”句。沈氏曾力陈假英款造铁路,劝翁同和开学堂讲新学,主张开设银行,开矿挖煤,派遣留学生,办造枪炮厂等等,无不赞成新政的。事实上,他的这些设想在晚清接二连三的政治活动中,影响力是很小的。沈曾植以忧世的心情做学问,终究不济世用。王蘧常先生在《沈寐叟年谱》中称其晚年:“日惟万卷埋身,不逾户阈,及闻国事,又未尝不废书叹息,欹觑不能自己。”一代硕儒那悲惨的身影跃然纸上。

在仕途上,光绪六年成进士,供职刑部十八年,先任贵州司主事,进为员外郎,后转江苏司郎中。迁任总理衙门章京,外简江西广信知府。由于柯逢时赏识,调任南昌府知府。后攫为安徽提学使、布政使,并护理巡抚。最显赫的是张勋复辟时,任学部尚书,但没几天,复辟失败了。总之,沈曾植虽硕学鸿才,而察吏理财,运用权术,非其所长也。或许是性格使然,或是清朝统治走向衰亡的征兆。
不过,在沈曾植任官经历中,有几件事是极其辉煌的:一是1895年,与康有为、陈炽、丁立钩、王鹏运、袁世凯、文廷式,张孝谦、徐世昌、张权、杨锐及其始沈曾桐在北京开强学会,开风气之先;二是1900年,因义和团起义闹事,沈曾植与刘坤一、盛宜怀、张之洞、李鸿章等人密商保护长江之计,所谓“东南互保”也。这其中,沈曾植出力甚多:三是1901年,出任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监督,兴办教育:四是1906年,东渡日本考察学务及文物制度,接触了许多新思想;五是1907年,在安徽设存古学堂,借鉴外国大学高等教育制度,实行“有研究而无课本,有指授而无讲解”的教学方法。他曾与杨仁山创佛学研究会,与欧阳渐创设支那内学院。凡此诸事,均反映了沈曾植的智慧与才能,也因此而奠定了前清遗老中大先辈的地位,人称他为“旧时代旧人物之鲁殿灵光”,一点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