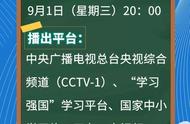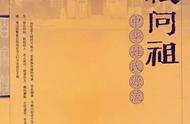沈曾植《行书韩世忠题雲居壁诗轴》
晚清整个社会都在求变求新以自强。沈曾植书法以占为变.以古为新,翻覆盘转,新意十足。历史上,米芾、赵左頫是以古为新的成功实践者。沈曾植在给门生谢凤孙的信中曾指出:“吾尝以阁下善学古人为不可及:今忽曰:以临古为大病,此涣何耶?来屏有使转而无点画,即使转办单薄寡昧,如此便是自寻贱落矣,如何?米元章终身不离临摹,褚公亦然,上至庚亮、谢安石,办有拟法。鄙人临纸,一字无来历,便觉杌不安也。”但沈曾植的复古意识与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等人比较起来,还是很有特点。米、赵、董复古以正统自勉,非二王不学,以取晋药为主,非“相杂文生”。所以,他们的书学思想中很难见到诸如沈曾植所主张的“异体同势”、“古今条形”、“中画圆满”、“分画中虚”这些内容。孙过庭所谓“古质而今研”,沈即是研了,更注重书法形式上的变化,注重参势而姿生的结果。
沈曾植之所以能独树一帜,除了上述的种种鲜明的见解外,还具有一颈勇猛精进的心。他在书学上没有像包世臣那样钻牛角尖,而是主张古今融合,南北相济,以期相生相发的境界。在实践上,他非常大胆地运用“抽锋”、“卧笔”之类的手段,如果用正统的眼光来看,觉得有些偏胜;如果用新理异态的效果来看,恰到好处。

沈曾植《草书右军桓公帖轴》
三 艺术成就
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把沈曾植的书法列为“帖学”的殿军人物,称“他是个学人,虽然会写字,专学包世臣、吴熙载一派,没有什么意思的;后来不知怎的,像释子悟道般的,把书学的秘奥一旦豁然贯通了”。这与王蘧常先生在《忆沈寐叟师》中称“先生生前先以书法为余事,然刻意经营,竭尽全力,六十四岁后始意写字。至七十三岁去世,用力极勤,遂卓然成为大家。” 二说大同小异,同的是称沈曾植大器晚成,不同的是一说沈中年之前“没有什么意思”;一说是“刻意经营,竭尽全力”。据沈曾植的生平经历来看,王说更接近些。据沈曾植自称晚年书画之缘始自光绪壬寅〔53岁)辞去南洋公学监督后,重入都门时。

沈曾植“早岁欲仿山谷,故心与手忤,往往怒张横决,不能得势。”(又马宗霍《霋岳楼笔谈》)但临池之志仍然无间矣。在未中举之前,学书以晋唐小楷为主,因为当时江浙——带文风鼎盛,多数士子为了中举,多练习所谓的“馆阁体”。以至于沈曾植晚年在回忆时还为“馆阁体”辩护,说:“唐有经生,宋有院体,明有内阁诰敕体,明季以来有馆阁书,并以工整见长,名家薄之于算子之誚,其实名家之书,又岂出横平坚直之外:推而上之唐碑,推而上之汉隶,亦孰有不平直者。虽六朝碑,虽诸家行草帖,何一不横是横、坚是竖耶?算子指其平排无势耳。识得笔法,便无疑己。永字八法,唐之闾阎书师语耳。作字自不能出此范围,然岂能尽。”(见《海日楼札丛》卷八)同时,他还得笔于包世臣,取径于邓石如、吴让之。沈曾植曾有诗曰:“百年欲超支吴老,八法重添历下读”,又云“包张传法太平时,晚见吴生最老师。”(见《忆沈寐受师》)所流露的正是这一阶段的学书痕迹。
之后,他又接受包世臣“备魏”可以“取晋”的观念,取法北碑,尤嗜张裕钊的书法,并确确实实练了一阵子。这与他在光绪六年成为进士,北上就仕,开始经营收罗一些碑帖,这是他后来自谓“书学深”的开始。当然,他对待碑帖的态度未必全是艺术的眼光,有时月考证舆地、史实的目的,但对他今后书法气质的演变有着积极的影响。即使成不了“书家之字”,尚可作“学人之字”观,这与他“学人诗人二而为一”的主张相一致的。
王蘧常先生把沈曾植的书风演变分为两个阶段:六十岁之前“为孙隘庭临《郑文公碑》,绝少变化;又见为予外舅沈公仲殷写佛经卷,当时诧为精绝者,亦不能过安吴轨辙。”(见《忆沈寐叟师》)六十岁之后,“真积力久,一旦顿悟,遂一空依傍,变化不可方物。”(同上)事实上,沈曾植学书情况比这样复杂多多,尤其是晚年。据目前所见的作品来看,沈氏取法简牍、唐人写经、《二爨》、钟太傅、索靖、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黄山谷、倪元璐、黄道周都有些痕迹,这说明他还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碑帖结合,兼容并蓄。值得注意的是1910,沈曾植在题《伊川击壤集》、《曹恪碑》、《李澹圆先生叱牍归耕图卷》三跋时,纯用米芾笔法,驾轻就熟,非常老到。从中可以透出两个消息:—中沈曾植借米芾书凤来达到“意态纵横”的目的,他推崇黄小仲的“始艮终乾”之说从中得到了验证;二是取法米芾正是他实现“备魏取晋”理想的绝妙高招。因为他一生的学术与人生总旨皆的魏晋风骨上。正是他从米芾那里悟到了“八面出锋”的用笔方法,并将米氏刷字转化为“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奇趣横生”(见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这才是他书法的奥秘所在。
沈曾植晚年的书法,包世臣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尤其庄用笔的提按方面,而张裕钊与吴让之的影响反而不怎么显著。罗振玉在916年6月5日致王国维的信中曾提及沈曾植“服赝安吴,诋毁赵之谦一事”,可与佐证。夏承焘在《天风阁学词日记》卷二中记载:“冒鹤老尝遇寐老曰:君笔诚奇纵矣,然不过以方笔为包安吴耳。寐老拍其肩曰:此安可为外人道。”此又一佐证。王国维有诗赞沈曾植的书法是“古意备张索,近势杂倪黄。”作为同时代的大学者,此话切中要害。沈曾植中晚年的徘徊,正是在寻找表达“古意”的手段。既要出新,有要备复古之意。所以,他找准了以“新理异态”而著称的黄通周与倪元潞作为师法的对象。黄潜在《花随人圣童摭忆》中也指出了这一点。他还经常临习一些冷僻的碑版,这与康有为《广艺舟双揖》中的观点如出一辙。他常自称“书学深而书功浅”,晚年遍临诸碑帖算对“书功浅”的弥补。实际上,他到最后还未完全定型化,仍在探索之中。

沈曾植《楷书临爨宝子碑轴》
沈曾植天资高,理想富,性格内敛,毅力坚定,“藏身巧密”背后涌动着艺术的激情。沈氏晚年隐居沪上,仕途失意,心情抑郁,以诗书遣日。1921年,他正式在上海鬻书自给,以解生计之困,“海内外辇金求书者穿户限焉”。目前,社会上所流传的作品办大多在最后几年所书写的:但风格上很少雷同,说明他不墨守一家,博收广蓄的心态。他作诗主张要通“三关”,最后一关足“元嘉”。如何通“元嘉关”,他在《与金潜庐太守论评书》中提到:“但将右军《兰亭诗》与康氏山水诗打并一气读。”可见其境界是在“活六朝”,“庶儿脱落陶谢之枝梧,含咀风雅之推激。”(见《安般簃集序》)此一想法,在他书法中也有,惜未能点破。抑或是他自认为未臻此境,不便提出而已,不得而知。后来,陆维钊先生一生浸淫北碑甚深,到晚年亦有叹识王字真谛太迟之慨。真可谓是英雄之见略同矣。
沈曾植书凤与众不同,在清季尤为突出。章士钊评为“奇峭博丽”,甚为恰当。其奇峭处在善于借章草隶势,翻覆盘转,跌宕沉雄;其博丽处在由博返约,新理自出。曾理自出。曾熙称:“(寐)叟读碑多,写字少。读碑多,故能古:写字少,故能生。古与生合,妙绝时流。”(见《忆沈寐叟师》)此话对错各半,对的是沈曾植“读碑多”,错的是“写字少”。沈曾植书法的生是因为结体上的夸张和用笔上的逆势,非写字少的缘故。他平日作书喜用锐笔尖锋,在他看来是“矫赵派末流之弊”,亦非故意为生。曾熙还认为沈氏书法“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同上)此话应改为“工处在博,妙处在丽,胜人处在不俗”更为妥当些:文人书法求“生”很容易堕成“狂怪”,若。生”能与古意结合,那“生”就不会涉乎怪诞。沈曾植的“生”间于突帖之间,既不类于碑之苍茫,又不以帖之柔转,处于交融状态。
沈曾植书法诸体皆擅,行草尤工:有人认为他的草书为“清三百年来第一家”,大概是基于清代无草书的考虑。事实上,沈曾植晚年没有一件非常严格的草书作品,大多介于行草之间。其行草书纵横驰骋,有杨少师之妙。清代自碑学盛行,书家皆究心篆隶,草书鲜有名家者,沈氏行草书尤为难得。康有为认为“其行草书,高妙奇变,与颜平原、杨少师争道,超佚于苏黄,何况余子。”(见<中华文史论丛>l987年第2期)沈氏行草书提的按幅度大,用笔又能翻转盘旋,极尽情性之跌害,开一代新风。王蘧常称沈寐叟作书“速度极快,笔力奇重。……执笔在手,盘旋飞舞,极其灵动。”(见《忆沈寐叟师》)可谓是生动的注解。据传沈曾值是主张转指执笔,一如包世臣,不知此说可靠否?如确凿的话,那末,沈曾植算是奇人奇书了。其成功处在于气质、体势方面的把握,胜人一筹。他晚年作书于点画呼应特别经意,证明他本人意识到了用笔的重要性。赵孟頫的“结字因时而宜,用笔千古不易”,是金针度人的。
关于沈曾植书法艺术成就,其学生金蓉镜、王蘧常都有过比较公允的评价,现迻录于下:
“即以八法言之,精湛淹有南北碑之胜、自伯英、季度、稿隶、丛冢吉石、无不入其奥窔。有清三百年中,无与比偶,刘文清且不论、即完白、蝯叟为蜾扁书,驰骤南北、雄跨艺苑, 亦当俯首。晚年应接品流、长 大卷,流而益雄。散落海上,如次仲一翮,山川为之低昂,可以知其书学之大概矣。”(全蓉镜语转引自《忆沈寐叟师》)
“师之书法,雄奇万变,实由读破万卷而未。所以予先论师之学问,然后再及于书,后之学先生书者,其在斯乎。”(王通常语见《忆沈寐叟师》)
沈曾植心目中非常向往魏晋冲夷淡泊的境界,毕生均未实现过。他投入书法的时间毕竟晚了点,更何况身处书道衰落的时代。陈定山称沈曾植的画“可以高妙,不可以精深;可以生拙,不可以纯熟。”正好说出了他书法的矛盾与局限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