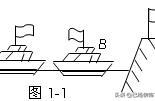不知道你小时候玩过“抓石子”的游戏吗?
先把十几个桂圆大小的石子放在地上,然后拿起其中一颗并迅速扔到空中,扔起的瞬间要迅捷、利落地抓起地上的一颗或多颗石子,其他石子必须保持位置不动,最后及时翻转手掌略微张开,趁空中那颗石子正巧落下来立马攥紧手。
碰动了其他石子或者没接住石子就算失败。
这是我上小学时和同学在课间乐此不疲的游戏。
小时候,我们村里一直有很多石子。
九十年代,村里人讨生计,先后搞过建窑、盖大棚、栽树苗、轧钢筋等等,前两项的结局是窑塌了,大棚被拆了。后两项,除了给极少数的人带来了经济效益,基本也都被放弃了。
最后一部分人把注意力放在了我们村的小山头上——嗑石子。
之所以说是小山头,是因为这块地面凸起远没有我家一百公里外巍峨的沂蒙山体魄庞大,小山头海拔区区100米,且是孤零零一小个。
但是这个平凡到可以在地图上忽略不计的小山头却给村里的孩子们无尽的乐趣。
春天,看着一冬的荒草慢慢翻出生命的绿色,奔跑在山路上寻找几株花朵盛开的桃树,山风都是温柔的味道。
最有趣的要数夏天。
雷雨过后,沿着路边湿漉漉的草地搜寻石头,猛地翻开,像开一个盲盒。翻出来“山水牛(一种带角的甲虫)”最让我们兴奋——全副武装、好斗又有点迟缓的甲虫憨态可掬;有时惊扰了蝎子的美梦,蝎尾高高举起,准备迎战不速之客,翻石头的人则会猛地抽回手、弹起身子来;最扫兴的是翻到蜈蚣,它那模样实在不讨喜。
有时奶奶会在雨后带我们拾“地角皮”——一种类似泡开的紫菜的菌类,回家冲洗干净,可以做成蛋汤。
最热的时候大人在山上压出打麦场,小孩子们把捆好的麦剁搭成小房子,钻到里面乘凉,白的、黄的蝴蝶轻轻飞过,抬起头来看日头,白晃晃的,让人更热了。
秋天要去摘酸枣。那些核儿大皮厚的酸枣长在叶片瘦小、满身硬刺、枝干永远只有筷子粗的野枣树上。这些枣树,与其说是树,不如说是荆棘丛,它们往往长在靠近悬崖边的石头缝里,采摘这些酸枣对小孩子们来说,算是一种安全的冒险——小心不被刺扎到,还不能离悬崖边太近。采了一大包,下山连忙拿给堂哥吃,拿给姐姐吃,有时吃到一棵熟透了、肉质饱满的,就像吃到蜜饯。
有时,我们姐妹还会和奶奶去山西面的坡地上挖地瓜。挖自己家地里的乐趣远远小于挖宝一样在别人家地头搜寻漏网之鱼。在表面上看起来已经收完的地里,耐心的挖、翻,忽然间刨出来一个小地瓜,就像地上捡到百元大钞。
冬天,大雪过后登山看雪最有趣。中学之后儿时的玩伴渐行渐远,有时一个人爬上山,纵目四望,寂寂无人,遍野的雪愈发圣洁,竟忍不住生出一些宇宙苍茫、人生如寄的感怀。
我们村子也大概因为这个小山头叫做“小山子”村。
这“小”,不仅是背靠的山头小,
我们村还是方圆几十里面积最小的村庄,狭长地沿着小山头从北向南分布,骑自行车南头到北头用不了十分钟。
我们村子很小,山头很小,村前的河也很小——是不知名的支流,有一个不甚宽的河道。
这个小小的村庄虽然小到常常被各大地图忽略,但是确实背山依水,山也好,水也好,回馈勤劳的人食物,还赠予孩子们无数乐趣。
等到村里的人开始建石子厂,有漫长的十几年,我都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
先是山上,然后是村北头,陆陆续续、先后有六七坐石子厂冒出来了(村里称为石子厂,实际上只是一个占地一间屋的机器加上大点的场地)。
红砖垒成房子一样的主体,一端是履带,从地上斜着往上延伸到顶端,类似滑雪场传送带,顶端下面预留了类似泳池的空间,碎石子就存在这里。
碎石头前先要炸山。
他们先在山上埋好雷管,然后在靠近村庄的山路上大声吆喝:“放炮了!”“放炮了!”“放炮了!”,靠山的人家听到后会迅速躲起来。
有时炸起的石子落到院子里或者瓦片上,发出脆利的声音,不由让人忧心石子可能伤人。所以这时不管小孩还是大人都会等“砰”的闷响过后在等两分钟,细听有没有石子落地,再照常活动。
一天大人们面色凝重,谈论家后面邻居的孩子。
大人说话不准小孩插嘴。
我不动声色的听着。原来那个妹妹被飞落的石子砸到了。
后来我再见到这个叫名字有梅的妹妹,那道疤从脸的一侧经过嘴巴直到下巴。我不敢和她对视,怕她以为我嘲笑她。
从我上大学起,我似乎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个妹妹,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是否婚嫁,是否做了手术祛疤?
炸完的大石头用拖拉机拖到石子厂,然后放到履带上,在轰隆声与粉尘味中,石子就被碦好了。或许是夜晚,或许是天没亮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石子拉走卖到我不知道的地方了。
这些在“石子厂”劳作的人,早出晚归。
傍晚时,一个短小精悍的叔叔得经过我们家门口回家。
他脖子上挂着毛巾,手里拎个水壶。不管毛巾也好,水壶也好,和他的头发上、脸上、衣服上一样,都像有一层蒙蒙的白灰。脸虽然洗过,但总感觉没洗干净。
他每次都迈着坦然、自信的步子,脸上挂着愉快又有点得意的表情——我从没看到过他显出疲惫不堪的样子。
他有一儿一女,儿子比我小太多我不了解,女儿比我大两岁,学习成绩一直很好,爸妈常常提起这孩子有多优秀,据说后来留在了南方的大城市。
有阵子不知什么原因,石头厂停工了。
石子厂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我们除了去挑用来玩“抓石子”游戏的石子,最喜欢在上面蹦跳。
石子堆的很高,基本可以够到最顶端,我们沿着坡爬上去,爬到机器下面的平台,然后再猛地蹦到石子堆上。也不觉得疼。
蹦累了我们就假装那是一个舞台,表演唱歌。
后来石子厂全部复工了。
天还没亮,就能听到拖拉机嘣嘣嘣地吵着出村子了。
有一阵子村民们很怕没风的天气。
有一次我从外面放学回家,骑车刚到能看到村子的路口,就发现整个村子被笼在“雾”中,但邻村和田地却没有雾。
走到村口,空气开始呛人,大量的粉尘直冲鼻腔。再往里走,整个村庄仿佛都在朦胧的雾中沉睡了。
回到家问妈妈怎么这么大的灰,妈妈说石子厂刮来的,好几天了。
妈妈很讨厌这些灰尘,她总抱怨,家里窗棂上没多久就会落满厚厚一层。
那时候的人缺乏安全意识和健康意识,没有戴口罩一说,不过是在牢*中逆来顺受罢了。
渐渐地,有石子厂开始停工。
慢慢地,只剩下少数几个“厂子”还在经营。
他们炸石头的位置已经很深、很远,深到地下水在岩层的裂缝里似隐私现,所以几乎不会再有提前的吆喝声。
嗑石子的人家富裕了,有的率先在村里盖起来二层小楼。
小山头在不知不觉间消失了。
从前爬上山之后有一个小高坡,孩子们都喜欢往上冲锋。
现在山头没有了,山枣没了,山水牛、蝎子也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又深又大、丑陋不堪的坑,仿佛陨石坠落的遗存,张牙舞爪,坑洼不平。
后来一个冬天午饭时间,大人们吃饭时又变得脸色沉重,说谁谁谁昨晚在山上失足坠崖死了,第二天才被人发现。村里传言,他家房子盖得太高太突兀了,风水不好。
我是个高中生了,可以在家发表意见,就问这人是谁。爸妈回答说是某某爸爸。
某某是我小学同学。
在那之后,偶尔的爆破声也渐渐消失了。
剩下的大坑沉默不语。这个丑陋的伤疤不仅留给了小山头,还留在了很多人心里。
等我们习惯了这个大坑,发现大坑也有一些聊胜于无的乐趣。
大雨过后,有的地方会存水,雨水多时深处足有一米,因为基底都是石头,几乎没有淤泥,就形成了天然大泳池。
炎热的午后很多男孩子会进去洗澡。
我们女孩会等没人的时候,踩着或锋利或陡峭或坑洼不平的石头去探那些水洼。
深的地方去不了,在一些积水没那么多的小水洼里洗洗脚脚也有意思,最奇妙的是这些水洼里有时会有成群的小鱼苗。
平时完全没水的山凹,怎么一下雨就冒出来鱼苗了呢?
冬天下雪时,又会存雪、结冰,成年后带着堂哥、堂姐家的孩子们去踩冰、砸冰,他们也玩得不亦乐乎。
再到后来我嫁人、为人母,回老家的次数愈发少了。
大坑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
前段时间区里响应国家恢复耕地政策,相中了大坑,给填平了,造了几十亩地。
一个近门的堂哥把地包去了。去年他们种了红薯。
有一次去姐姐家,姐姐特地把从堂哥那里买的红薯煮给我尝,因为有“小时候”的味道——又面又甜。姐姐说她已经让爸妈给买了十几袋,这地瓜卖的特别好,每次进城都被一抢而空。
我回老家时也买了十袋,带回城里,老公、公婆都说好吃。再让爸妈买时,已经卖光了。
清明节时回老家,和姐姐、堂妹带孩子到山上玩。妹妹说,小时候在石子厂蹦上蹦下居然也不觉得疼!现在才发现小时候爬山走的那条道那么陡(近九十度、三米高的斜坡),现在是断然不敢爬了。
我想起来有一次和堂妹、弟弟下山时走那个坡,我从上面滚了下来。坡下两三米处就是一个五六米深的大坑,而我从坡上滚下来竟然安然无恙,且滚到大坑边沿就停了下来。大概是有神灵护佑吧。
说给堂妹听后,堂妹哈哈大笑。
我想,这种在山上、田间,随意撒欢、纵情冒险、无拘无束的快乐,如果我们的孩子也能体会到就好了。
找记者、求报道、求帮助,各大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壹点情报站”,全省600多位主流媒体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