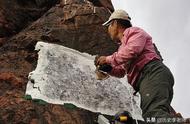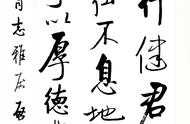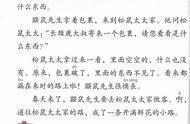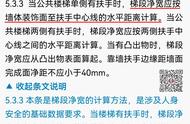如所周知,元人《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以下简称“沿革例”)的以下记载历来受人重视,被认为是研究宋元时代经书刊刻史事的重要线索:
今以家塾所藏唐石刻本、晋天福铜板本、京师大字旧本、绍兴初监本、监中见行本、蜀大字旧本、蜀学重刊大字本、中字本、又中字有句读附音本、潭州旧本、抚州旧本、建大字本、俞韶卿家本、又中字凡四本、婺州旧本、并兴国于氏、建余仁仲,凡二十本,又以越中旧本注疏、建本有音释注疏、蜀注疏,合二十三本,专属本经名士反复参订,始命良工入梓。[1]
不过,“蜀学重刊大字本、中字本、又中字有句读附音本”的说法,令人稍感违和——是历史上未曾有过“蜀学重刊小字本”,还是它未被纳入校勘范围?若是前一种情况,“中”必然小于“大”,既然不存在更小的“小”,“中字本”之称就显得没有着落,为何不径直谓之“小字本”?同理,“中字有句读附音本”、“又中字凡四本”,它们被称为“中字”的立足点是什么?
以上疑问的提出,显然是基于比较关系下“大小相对”的逻辑认识。强化这一思维定式的,是常见于善本书志题跋的“每半叶十行,每行大字十八、小字二十四”、“板心上注每纸大小字数”云云。此类记录至晚在清代中期便已出现,做法更是沿袭至今。它向人们施加了长远的影响,以至于提及版刻中的大字、小字,经它规训的人们(或者说是我们)的第一反应便是版面上同时呈现而大小有别的正文与注文。
但在逻辑上,除了比较意义上的相对差别,大/中/小字还可具有另外两种层面的含义:一是主观视觉感受,二是具体的尺寸规格(类似于衣物的S/M/L码)。这两者又存在关联,在某种程度上,尺寸规格脱胎于(或者不能背离)视觉感受。譬如,规格意义上的大字,人们的观感至少应是“不算太小”。
一旦明了存在多元意义之可能,便会引起如下警觉:版本学的研究语汇“大/中/小字”,是后代学者施加于版刻实物的“后见之明”,它的所指与宋元刻书语境下的“大/中/小字”完全一致么?若否,刻书历史现场中的“大/中/小字”,当作何解?本文拟就此提出初步假说。
一、文献中所见版刻语境下的“大/中/小字”
翻检宋代文献,不难发现刻书语境下的“大/中/小字”的记录。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著录“影北宋本”《伤寒论》(现藏台北“国家图书馆”),该本有北宋元佑三年(1088)国子监牒文,涉及当时国子监刊刻一批医籍的细节:
国子监准尚书礼部元佑三年八月八日符:元佑三年八月七日酉时,准都省送下。当月六日,敕中书省勘会。下项医书册数重大,纸墨价高,民间难以买置。八月一日奉圣旨:令国子监别作小字雕印。内有浙路小字本者,令所属官同校对,别无差错,即摹印雕版。并候了日,广行印造,只收官纸工墨本价,许民间请买,仍送诸路出卖。奉敕如右,牒到奉行。前批八月七日未时,付礼部施行。
续准礼部符:元佑三年九月二十日,准都省送下。当月十七日,敕中书省、尚书省送到国子监状。据书库状,准朝旨,雕印小字《伤寒论》等医书出卖。契勘工钱,约支用五千余贯,未委于是何官钱支给,应副使用。本监比欲依雕四子等体例,于书库卖书钱内借支。又缘所降朝旨,候雕造了,令只收官纸工墨本价,即别不收息,虑日后难以拨还。欲乞朝廷特赐应副上件钱数支使,候指挥。尚书省勘当,欲用本监见在卖书钱,候将来成书出卖,每部只收息一分,余依元降指挥。奉圣旨,依国子监,主者一依敕命,指挥施行。
治平二年二月四日进呈,奉圣旨镂版施行。[2]
治平二年(1065),《伤寒论》“奉圣旨镂版施行”,因是大字刊刻,导致印出的本子“册数重大,纸墨价高,民间难以买置”。是以元佑重刻《伤寒论》等书,特别要求“国子监别作小字雕印”,以便“民间请买”。
既然使用“小字”刻印是为降低成本/售价,那就不是字形略微缩小的问题,而是必须形成明显差距,足以达到以下效果:若行款不变,版面尺寸(对应版材尺寸)与书册开本(对应纸张尺寸)明显缩小;或版面尺寸大致相同,叶面字数大幅增多,叶数(对应版片数量)明显减少。无论何种方式,目的均为降低刻版印刷所需版材与纸张的消耗量。如牒文所云,浙江已用小字刻印了这批医书的一部分;甚至可以推论,“浙路小字本”不仅用于校对讹误,也是此次国子监“小字雕印”的面貌规格的参照物。要之,此处的“小字”是指足以影响刻书成本的字形规格。

左为宋嘉定六年章贡郡斋刻本《楚辞集注》,版框高19.2cm;
右为宋绍熙四年吴炎刻本《东莱标注老泉先生文集》,版框高19.6cm。
这是将二者版框缩放至约同等大小后的对比图,可见字形较小者的叶面字数远多于字形较大者。
胄监虽被推为两宋刻书之标杆,但刻书仅是其职责范围的一小部分,甚至很难说是日常事务,论长年累月唯以刻书为务,自无法与书坊相比。作为规格的“大/中/小字”,必是在刻书业内部自然形成,而非源自朝廷官署。如下引文,“鬻书者”敏锐发现潜在需求,制作出大受欢迎的“中字”,阅读体验优于“巾箱”(小字),价格低于监本(大字),是异于后两者的新规格:
《吕陶记闻》云:嘉佑、治平间,鬻书者为监本字大难售,巾箱又字小,有不便,遂别刻一本,不大不小,谓之中书《五经》,读者竞买。其后王荆公用事,《新义》盛行,盖中书《五经》谶于先也。[3]
《皕宋楼藏书志》卷四五著录宋刻本《重校证活人书》,该本今存日本静嘉堂文库,载政和八年(1118)朱肱序,中称:
过方城,见同年范内翰,云:《活人书》详矣,比《百问》十倍,然证与方分为两卷,仓卒难检耳。及至睢阳,又见王先生,云:《活人书》,京师、成都、湖南、福建、两浙,凡五处印行,惜其不曾校勘,错误颇多。遂取缮本,重为参详,改一百余处,及并证与方为一卷,因命工于杭州大隐坊镂板,作中字印行,庶几缓急,易以捡阅。……政和八年季夏朔,朝奉郎提点洞霄宫朱肱重校。[4]
宋刻本《六甲天元气运钤》,卷前有朱肱《运气图序》,题署官衔亦为“朝奉郎提点洞霄宫”,可知与上引序文写作时间相近,称:
今作小字镂板,非特广其传而巳。庶使一偏之士蔽于人而不知天者,知此书之不可不读也。朝奉郎提点洞霄宫朱肱序。[5]
朱氏对刻本面貌有自己的规划与掌控,此用“中字”,彼用“小字”。这两次刻书不相关涉,所以“中字”“小字”是对于物质性规格的指称,而非相对比较。可惜对应的北宋刻本,今已不存,无从得知自行规格的具体情况。
再看南宋时期之例。朱熹的多种著作在其生前刊刻,有些甚至经多次刊刻,可以说他与书籍刻印的关系匪浅。淳熙六年(1179),他致信吕祖俭,[6]称所著《论孟精义》将以“大字版”刊印。此时,书尚未付梓,“大字版”不是呈现于眼前的视觉感受,而是规划中的面貌:
豫章欲刻《精义》大字版,意欲令并刻老兄所増横渠诸说。此间传录未及数篇,专作此数字,今后遣人就借,得以付之为幸。[7]
明弘治十一年陈宣刻本《二程全书》的附录部分,收录了一些早期刻本的序跋,中有淳佑六年(1246)赵师耕序,称自己本次刻书改用“大字”:
河南二程先生《文集》,宪使杨公已锓板三山学宫。《遗书》《外书》,则庾司旧有之,乙未之火,与他书俱毁不存。诸书虽未能复,是书胡可缓。师耕承乏此来,亟将故本易以大字,与《文集》为一体刻之后圃明教堂。赖吾同志相与校订,视旧加密,二先生之书于是乎全。时淳佑丙午古汴赵师耕书。[8]
明嘉靖间覆刻宋阮仲猷种德堂本《春秋经传集解》,在清代长期被误认为宋刻原本,致误原因是该本卷末照刻了淳熙三年阮氏刻书牌记,牌记称所刊为“大字”:
谨依监本写作大字,附以《释文》,三复校正刊行,如履通衢,了亡室(窒)碍处,诚可嘉矣。兼列图表于卷首,迹夫唐虞三代之本末源流,虽千岁之久,豁然如一日矣,其明经之指南欤。以是衍传,愿垂淸鉴。淳熙柔兆涒滩中夏初吉,闽山阮仲猷种德堂刊。
以上三例,大体涵盖了南宋刻书的三大类型:种德堂本自是坊刻,赵师耕刻本有浓厚的官刻意味;朱熹可插手指挥豫章本的刊刻事宜(“意欲令并刻老兄所増横渠诸说”),与主事者当有交谊,考虑到他的身份地位,此本或官刻或私刻。三家均称使用“大字”,大约是因为刊刻成本较高,阅读体验良好,是值得表出的自豪之事。
通观上揭诸例,可感觉到:在刻书语境下,“大字”“中字”“小字”是指特定的尺寸规格。惟与之对应的刻本实物皆不传,无从确知具体尺寸数值。以下将考察文字指称与刻本实物可相对应的若干实例,探索这一问题。
二、宋元时代的“中字”:实例与分析
先看元泰定元年(1324)西湖书院刻本《文献通考》。其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分记两种字形时,绝大多数叶面以“中(字)若干”,指称正文字数。[9]通计全书,作“大(字)”者,仅129叶,涉及刻工十余人;[10]作“中(字)”的叶数,至少是十倍以上,对应的刻工人数远多,且有多人见于其他元刻本。[11]
须说明的是,该本没有尺寸更大的第三种字形,故而“中字”决非基于比较关系的相对性称谓,而是指字形的尺寸规格。刻工们非常清楚,自己刻制的是“中字”与“小字”,工毕核算报酬,依照这两种规格的标准分别计算,所以“物勒工名”,留下了这些记录。正因“中若干小若干”是未经后世扰动的原始工作痕迹,便为探究元代刻书业的字形规格,提供极为难得的、可信的观察基点。
既然谈论规格,就必须给出具体数值。受汉字形体结构与手工生产的双重影响,刻本中各字的高广势不能整齐划一,宋元刻本的上下字之间往往笔划交错,测量时难于取准;加之调阅宋元刻本实物,逐字逐叶测量,更缺乏可行性。是故,本文的方法是将版框高度除以每行字数,版框宽度除以每叶行数,得出每字平均可用空间;由此摆脱上述细节干扰,更利于宏观把握总体情事。
回到西湖书院本《文献通考》。该本十三行二十六字,版框26×19.2cm,[12]照上述原则计算,平均每字可用空间为1×1.48cm。[13]此本少数叶面称“大字”,绝大多数称“中字”,可见它正处于两种规格的临界线的“中字”一侧,所以可初步判定,高度1cm是元代浙江地区刻书业“中字”规格的上限。

《文献通考》元泰定元年西湖书院刻本,此叶版心标记“中五百九十,
小三十一”(图片引自《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

此叶全为正文,版心标记“中字三百四十一”,刻工付茂又见元至正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刻本《宋史》《金史》。
在新刻书以外,西湖书院收储大量南宋旧版,修补重印,其中也有一些反映“中字”实态的史料。
宋刻递修本《春秋公羊疏》《尔雅疏》,为南宋前期浙刻本,与南宋国子监关系密切,元时版片在西湖书院。前者现存卷一至七(国家图书馆藏本),有2叶版心标记“中若干”,均为元代补版。后者(国家图书馆藏本)以洪武公文纸刷印,有8叶版心标记“中(字)若干”(均为补版),其中3叶可辨识刻工姓名,为李宝、俞声、徐荣。案,李、俞为元代刻工,见于多种宋刻本的西湖书院补版。[14]徐荣补版叶及卷十叶12(无刻工姓名),字体风格似为宋刻。[15]卷三叶3,字体与以上各叶明显不同,应是元末甚至明初的补版。
它们的规格是:《尔雅疏》,十五行二十九至三十一字,版框20.1×15cm,平均每字0.67×1cm。[16]《春秋公羊疏》,十五行二十二至二十八字,版框21.9×16.8cm,平均每字0.88×1.12cm。
南宋初刻递修本《通典》,亦为浙江地区刻书,风貌与《尔雅》《公羊》单疏本类似,与南宋国子监有关。元代补版叶有标记“中若干小若干”者,刻工姓名模糊难辨,然《西湖书院重整书目》有载,可断定乃西湖书院补版。该本十五行二十六至二十八字,版框22.8×16.5cm,平均每字0.84×1.1cm。
宋刻递修本《冲虚至德真经》亦是南宋前期江浙地区刻本,国家图书馆藏本有4叶元代补版标记“中若干小若干”(其中2叶署名“蔡”、“贵”)。原刻叶与补版叶的字体版式风貌,与《尔雅》《公羊》单疏本接近,虽不载于《西湖书院重整书目》,但补版时地宜与之相差不远。该本十四行二十五至二十六字,版框21.8×15.3cm,平均每字0.84×1.09cm。
如所周知,补版一般不会变动行款,版框尺寸亦与原刻相近,故而补版叶与原刻叶的字形规格基本相等。既然按照元人的标准,以上诸书的补版叶为中字,然则宋人视原刻叶为中字的可能性,就值得充分考虑。但是,西湖书院补版,距宋室覆亡已有数十年之久,不能遽以之等同于南宋的情形——尽管其他方面的实例证明,刻书业的某些习惯做法长期不变。[17]
可幸的是,南宋“中字本”也有可信实例。淳熙三年(1176),张杅于江南东路广德军任上刊刻《史记集解索隐》,世称桐川郡斋本,卷末张杅跋称“因搜笥中书,蜀所刊小字者偶随来,遂命中字书刊之”。这是刻书发起人自我声称的“中字本”,绝无可疑。该本十二行二十五字,版框19.2×14.9cm,平均每字0.77×1.24cm。
出现于嘉德公司2005年春季拍卖的宋刻附释文本《春秋经传集解》,被认为是《沿革例》提及的蜀刻“中字有句读附音本”。该本十一行二十字,版框20×14cm,平均每字1×1.27cm。[18]
以上两种南宋中字本,恰好落在元代“中字”规格的数值区间内,可见宋元刻书业的“中字”规格一脉相承,进而可证《春秋公羊疏》等书,系宋人以彼时“中字”规格开雕。
综上诸例,可暂作小结:“中字”规格不是某一固定数值,而是一定的范围区间,这是雕版印刷作为手工业生产的必然特性。宋元刻书的“中字”规格基本相同,范围约在每字(高度)0.7-1cm之间,0.8-0.9cm者居多。
三、南宋刻书中的“大字”:实例与分析
辨析“大字”规格,较“中字”为难。症结在于:序跋牌记称“大字”者,相对可信,但实例不多,无法全面说明问题。以版心标记“大若干小若干”为据,无法在逻辑上彻底排除比较意义之“大小”的可能性(“中若干小若干”无此歧义困扰);反之,亦无法从逻辑上彻底排除指称规格的可能性,若能举出大量实例,仍可有一定信度。
有鉴于此,先观察序跋牌记自称“大字”的实例,确定初步的可信范围。宋宝佑五年(1257)湖州刻本《通鉴纪事本末》,赵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