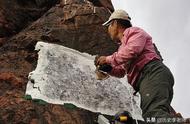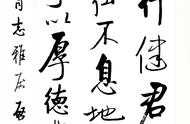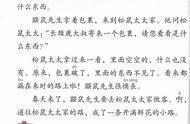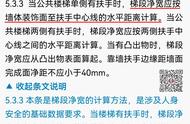左为《仪礼集说》,右为《文献通考》,均为国家图书馆藏本。
《文献通考》此叶无双行注释,版心标注“中字三百四十一”。
至于西湖书院以外的元代刻本,先看序跋刊语提供自述材料的一例。元至正五年抚州路儒学刻本《雍虞先生道园类稿》,前有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司刻书牒文,称“如蒙移文本路,详加编录,大字刊行”云云。该本九行二十字,22.8×15.3cm,平均每字1.14×1.7cm。[31]
下表诸例均有元刻叶标注“大若干小若干”。尽管样本有限,但仍可看出元代后期刻书的“大字”规格,似在缩小(虽尚有尺寸较大者如《金陵新志》)。这与南宋“大字”规格不呈时代性变化,有所不同。此外,《孟子》相台岳氏刻本、盱郡刻本,均为翻刻宋廖氏刻本,岳本、盱郡本又与廖氏刻本《河东先生集》行款一致,规格相近;由此可知,廖氏九经与韩柳集采用同一规格,岳氏、盱郡翻刻时沿用廖氏的原始规格。可见“大字”与否,还会与原刻翻刻有关;这与补版叶的规格近似原刻叶,其理相通。

五、宋元坊刻的“大字”
前揭实例多为官刻本、私刻本,受其性质影响,序跋刊语自我声明“大字”者较少。坊刻本有商业宣传的需求,乐于做此类宣传,故而留下了不少实例:
饶州德兴县庄溪书痴子董应梦重行校证,写作大字,命工刊板,衠用皮纸印造,务在流通,使收书英俊得兹本板,端不负于收书矣。绍兴庚辰除日,因笔以记志岁月云。[34]
饶州德兴县庄溪董应梦宅经史局逐一校勘,写作大字,命工刊行。(以上宋绍兴三十年饶州德兴县董应梦刻本《重广眉山三苏先生文集》刊语)[35]
先生父子文体不同,世多混乱无别,书肆久亡善本。前后编节刊行,非繁简失宜,则取舍不当,鱼鲁亥豕,无所是正,观者病焉。顷在上庠,得吕东莱手抄凡五百余篇,皆可诵习为矜式者。因与同舍校勘讹谬,别为三集。逐篇指摘关键,标题以发明主意。其有事迹隐晦,又从而注释之。诚使一见本末不遗,义理昭晰,岂曰小补之哉。鼎新作大字锓木,与天下共之。收书贤士,伏幸垂鉴。绍熙癸丑八月既望,从事郎桂阳军军学教授吴炎济之咨。(宋绍熙四年吴炎刻本《东莱标注老泉先生文集》牌记)[36]
此书系求到京本,将出处逐一比校,使无差谬,重新写作大板雕开,并无一字误落。时庆元丁巳之岁建安余氏刊。(宋庆元三年建安余氏刻本《重修事物纪原集》牌记)[37]
万卷堂作十三行大字刊行,庶便检用,请详鉴。(宋万卷堂刻本《新编近时十便良方》卷末刊语)[38]
本家今将前后汉书精加校证,并写作大字锓板刊行,的无差错。收书英杰伏望炳察。钱塘王叔边谨启。(宋王叔边刻本《后汉书》牌记)
今将伊川先生点校古本逐卦附入陆德明释音,写作大字刊行,刻画精致,并无差误。收书贤士伏幸详鉴。(宋末建阳刻本《伊川先生点校附音周易》牌记)[39]
两坊旧刊诗书集传,俱无音释,览者有遗恨焉。本堂今将书传附入鄱阳邹氏音释,诗传附入金华许益之名物钞音释,各依名儒善本点校句读,仍取纂图,置之卷首。大字刊行,精加校正无差,庶几读者豁然无疑矣。与坊中旧本玉石判然,收书君子幸监。至正丙午孟冬梅隐精舍谨识。(元至正二十六年梅隐精舍刻本《书集传》牌记)[40]
坊刻本以盈利为目的,成本是重要问题。即便刻制“大字”的费用与“小字”持平,[41]前者也意味着更大尺幅或更多数量的版面,导致版材与纸张成本增多。从善意角度理解,既然宣称是“大字”,为免名不符实之诮,总不宜与当时人们对“大字”的普遍认知相差过远;好比现代人指着小五号字而谓之“大字”,无疑相当尴尬。但如下表所示,以上号称“大字”的坊刻,规格与官刻私刻相差甚远,大多仅相当于前者之“中字”。

由此,话题可转回至西湖书院。不少刻工见于西湖书院补版/新刻的多种书籍,各书的刻工又不尽相同。这暗示了:当时存在专以刻字为生或主要生计的刻工群体,人员相对稳定,而书院与刻工的关系松散,欲刻书补版,方临时募集,故甲书有张王李赵,乙书有赵钱孙李。刻工平日为他处/他人刻书,最可长期服务的便是书坊。正是在书坊的工作经验——1cm的规格在坊刻中足可夸称为“大字”,使一部分刻工习惯成自然,在《文献通考》中留下了“大若干小若干”的记录。
如下表所示,也有部分坊刻本“大字”与官刻私刻不相上下。[45]这或与翻刻本尺寸规格近似原刻有关,如宋十行本与元十行本、蔡琪本与白鹭洲书院本皆是。

综言之,宋元坊刻的“大字”看似模糊而宽泛,低者可下探至官刻私刻的“中字”区间;这似乎暗示坊刻另有一套字形规格。但无论官私坊刻,均由当时的工匠群体承担刊刻;而刻字规格作为行内的约定俗成,不太可能随服务物件的变更而改变。有趣的是,以笔者见闻所及,除了前述“中书《五经》”,未见坊本自称“中字”或“小字”,凡自我声明者,均称“大字”。可见从商业宣传的角度考虑,“中字本”与“小字本”不值得夸耀。然则,坊刻“大字”规格的含混,更多是书坊的经营策略,向潜在顾客宣称“大字”刊行,与实际按“中字”规格刻版及议价付酬,并不相悖。
余论与小结
行文至此,可能会引发质疑:为何宋元刻书“中字”与“大字”的临界线,偏偏落在公制长度1cm?“小字”规格如何,文中何以未论及?
这两个疑问存在关联,因缺乏足够证据,仅能略作推测。“大/中字”的临界点,可能是尺制下的三分,1宋尺约31.2~32cm,3分为0.954~0.96cm,与公制1cm极接近。沿此进一步推论,前述“中字”诸例的最小者为0.67cm,结合宋代尺制考量,“中/小字”边界似为2分(0.624~0.64cm)。
讨论“小字”之难,在于文字证据与版刻实物之对应。如前述,序跋牌记的自我宣称相对可靠,故本文论述“大/中字”时,先以此类材料为据,确定初步范围,再辅以版心标记,进行细化。“小字”不值得自夸,序跋等避而不提,无法在现存版本中找到自我宣称的实例;版心标记“大若干小若干”,数量虽多,但按本文计算方法,前揭诸例的双行小字注文,多符合“中字”规格。——这似有推翻本文观点的危险。
笔者对此的理解是:本文计算得出的是平均每字可用空间,而非每字平均大小。宋元刻本的(正文)字距较紧,乃至笔划交错,两者相差不大;而双行注文须迁就正文大字,与之形成相当的大小等差,且双行间要留出间距,实际字型往往小于可用空间不少。另一方面,某些“大字本”的正文字型很大,若注文坚持“小字”规格,大小悬殊,比例失调,有欠美观,遂不得不有所折中。
当然,这不意味“小字”是空悬之物,或符合“小字”规格的宋元刻本已无存世。
如开篇所述,“小字”可显著降低成本,是故宜于成本敏感型的低端商业出版物中觅之。正如当今的商业活动强调细分市场,宋元时代同样存在高度发达与专业细分的出版市场。坊刻亦不一味徘徊于低端,书坊会针对不同消费能力与需求的人群,精准投放产品,故而版刻在各方面均呈现极大跨度,其中最易被感知的是技艺与视觉效果。顶级坊刻之精工,毫不亚于官刻私刻,如余仁仲、黄善夫、陈解元诸家所刻书,相比茶盐司、世彩堂刻本,风格固然不同,堪称精品则一。而金刻本《刘知远诸宫调》(十二行二十至二十一字,版框10.3×7.8cm,平均每字0.5×0.65cm)、元刻本《古今杂剧》(十四行二十四至二十七字,版框13.7×9.3cm,[48]平均每字0.54×0.66cm),内容、开本、版式布局、刻字水准均远逊于前揭诸书,可以视为宋元低端版刻的代表。无不巧合的是,其字形规格亦低于上文推测的“中/小字”临界线。[49]在历史的冲刷下,“小字”的主要运用场景——低端版刻的幸存几率极低,因而关于“小字”,只能止步于以上推测。
要之,在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中,“大/中/小字”原是历史上的版刻术语,藏书家/版本学者在版刻实物中观察到了它们,并用以指称所欲指称,在此移用过程中,词汇的含义发生了偏转,加之日益远离宋元版刻生产的语境,“大/中/小字”的原初含义,反致湮没无闻。理解此点之后,就会对《沿革例》等文献中的“大字本”“中字本”“小字本”,有更加深刻而鲜活的认识。
本文所作研究,须调查大量版本,并逐叶翻检。调查宋元本实物,存在难以逾越的客观限制,版心又往往破损难辨。所幸各处公布的电子资源日增,笔者尽力搜得并析出前揭各例。然而书海无涯,我愿意随时修正(而非撤回)自己的观点。
[1] [元]岳浚:《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北京:北京大学2019年影印清影宋抄本,第2页。
[2] [清]杨守敬撰,张雷校点:《日本访书志》卷九,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1页。
[3]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六,此例承董岑仕女士见示。
[4][清]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四五,清光绪间归安陆氏刻本,第17页a。
[5] [宋]佚名:《六甲天元气运钤》,《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影印宋刻本,第1页a。
[6]此函系年用陈来之说。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173页。
[7]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一,《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影印宋咸淳元年建安书院刻宋元明递修本,第11页b。
[8] [宋]程颢、程颐撰,[明]康绍宗编:《二程全书》卷六四,明弘治十一年陈宣刻本,第13页b-第14页a。此序后有小字注“麻沙本后序”。案,以序中“庾司旧有之”、“师耕承乏此来”、“刻之后圃明教堂”等语观之,赵氏刻本似为官刻。盖麻沙坊本从赵本出,而保留赵序。淳佑六年,赵氏所任何官不明,明年则转任知泉州事。《道光晋江县志》卷二八“历代泉州府以下职官考”,淳佑七年八月,知泉州事陈大猷致仕,师耕接任。又,泉州九日山摩崖石刻有“淳佑丁未(七年)仲冬二十有一日,古汴赵师耕以郡兼舶,祈风遂游”,可知他兼任提举市舶司。
[9]此本共6200多叶,版心标记字数者占多数。整叶全为正文或双行注文者,记作“若干”,兼有正文注文者则分记。分记的格式用语不一,有“若干小若干”、“若干,若干”、“大若干小若干”、“中若干小若干”、“若干中字若干小字”,等等。
[10]刻工姓名多仅署一字,如翁、吴、阮、良、公、寿等,难以确定分合,署双字者有君仲、正方、子华、子坚。
[11]如王子仁、付茂、陈福、陈大用等人,亦见于元至正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刻本《宋史》《金史》,张以方参与刊刻元泰定二年庆元路儒学刻本《困学纪闻》。
[12]文中的版框尺寸资料,凡未说明者,均取自《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
[13]此处尚须说明。尽管资料上横大于纵,但绝大多数宋元刻本的字体不呈明显的扁方状,这是因为:按照本文的计算方法,纵向尺寸、横向尺寸实际分别包含行间距与字间距,但宋元刻本上下字之间往往笔划交错,字距较小,行间距则相对疏朗。职是之故,更接近字形实际大小的是资料中的纵向尺寸(高度)。
[14]李俞二人并见于小字本《说文解字》、赣州军学本《文选》,李宝又见于所谓“眉山七史”本《宋书》《陈书》。
[15]根据尾崎康的研究,南宋前期江浙刻本南北朝七史(即“眉山七史”)之南宋中期补版刻工有徐荣,元代中期补版刻工亦有名徐荣者。参见尾崎康着,乔秀岩、王铿编译:《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12-114页。
[16]每行字数取中位数即三十字计算,以下同。
[17]石祥:《小样:中国古籍刻印中的局部印刷》,《古典文学知识》2019年2期,第70-75页。
[18]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85-191页;拓晓堂、傅敏:《破解七百年的谜局——宋蜀刻中字本<春秋经传集解>介绍》,《中国商报》,2005年7月14日第1版。
[19]版框尺寸数据,引自“国立故宫博物院”:《故宫图书文献选萃》,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73年,第65页。
[20]静嘉堂文库藏本的版框数据,均引自静嘉堂文库:《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东京:汲古书院,1992年。
[21]《诗集传》《中庸辑略》虽无序跋牌记刊语等文字证据,但两书行款相同,字体风貌均是浙刻风味,且各有多名刻工见于《绍定吴郡志》 、大字本《通鉴纪事本末》。刊刻《本末》之宝佑五年,已属理宗在位(1224-1264)之后期。由此推测,此二书应系理宗时浙地所刻,且可能存在关联。
[22]世彩堂本韩柳集行款一致,尺寸相仿,仅取柳集为例。
[23]抚州公使库所刻诸经,行款并同,尺寸相近,仅举《礼记》为例。
[24] http://db.sido.keio.ac.jp/kanseki/T_bib_body.php?no=006973
[25] http://db.sido.keio.ac.jp/kanseki/T_bib_body.php?no=006744
[26]韵书版式特殊,取卷一“韵例”统计行款。
[27] http://db.sido.keio.ac.jp/kanseki/T_bib_body.php?no=006956
[28]统计时,包括了下文所述的宋刻元修本,下统计图同。
[29]作为参照,《永乐大典》开本高近50cm,观览实物,可知其庞大已有碍阅读。又,以上诸例规格在1.5cm及以上者,每行字数多为十五六字,行数多为六至八行,便是有意减少版面总字数,以控制版面尺寸。
[30]同等条件下,每字相差2毫米,书叶整体的视觉差异将相当明显,熟悉版刻实物者自可理解。
[31]《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编辑出版委员会:《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6072页。
[32]此本版心不标字数,为便比较而列出。
[33]昌彼得:《增订蟫庵群书题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1页。
[34] [宋]苏洵、苏轼、苏辙:《重广眉山三苏先生文集》卷二八,《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影印宋刻本,第9页b。
[35] [宋]苏洵、苏轼、苏辙:《重广眉山三苏先生文集》卷三二,第7页b。
[36] [宋]吕祖谦:《东莱标注老泉先生文集》目录,《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影印宋刻本,第4页b。
[37]静嘉堂文库:《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图版编,第165页。
[38]北京图书馆:《中国版刻图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61年,图版二三二。
[39]http://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SearchDetail?item=1128886719614279a5617126f2bdf086fDM5ODk40&image=1&page=&whereString=&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
[40]“国立故宫博物院”:《邻苏观海院藏杨守敬图书特展》,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2014年,页66。
[41]宋元时代的刻书资费标准难以确知,既然标称“大若干小若干”,不同规格字形的资费当有不同。作为参考,王季烈《江苏苏州莫厘王氏家谱》收录《乾隆修谱纪略》,称:“三月十一日,往穆大展店,用白木板刻宋字,讲价中字每百八分,小字每百六分。抄写样稿毕,送阅勘正,然后付梓。”(卷十二,民国二十六年石印本)穆大展是乾嘉时苏州刻字店主,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资费标准中也出现了“中字”。
[42]北京图书馆:《中国版刻图录》,第45页。
[43]http://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SearchDetail?item=1128886719614279a5617126f2bdf086fDM5ODk40&page=&whereString=&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0&HasImage=
[44]“国立故宫博物院”:《邻苏观海院藏杨守敬图书特展》,第66页。
[45]除宋十行本《监本附音春秋谷梁注疏》,各书均有叶面标注“大若干小若干”。
[46] http://db.sido.keio.ac.jp/kanseki/T_bib_body.php?no=043744
[47]白鹭洲书院刻本,中国学者多认为是宋刻本,本文采用尾崎康的观点,他认为此本是蔡琪刻本的元代翻刻本(《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第340-341页)。
[48]此据《中华再造善本》卷端给出的资料,《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称版框19.3×13.7cm,有误。
[49]当然,不能仅凭“小字”断定“低端”。如天禄琳琅旧藏宋刻巾箱本《礼记》,十行十九字,版框9.6×6.8cm,平均每字0.51×0.68cm;此本刊刻颇精,足堪赏玩,是刻意为之的高端袖珍书。
【作者简介】
石祥,1979年出生,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青年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