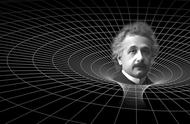看过《儒林外史》的读者一定会记得书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严监生。他临死前还惦记着“两茎灯草”迟迟不肯断气,而成为了中国“吝啬鬼”的典型。

临死前的严监生
我们首先来看下《儒林外史》作者的档案:吴敬梓,男,汉族,安徽滁州人。年少聪慧,善于背书,最喜欢一本书是《文选》。一生经历了清朝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三代。性情豪放,属性“败家”。父亲死后被来“打秋风”的亲戚朋友将万贯家财挥霍一空,几近粮绝。

虽然将家财败尽,可这并不意味着吴敬梓就是一个糊涂的人。相反他十分清醒,这一点从他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中就能看出。鲁迅对《儒林外史》有这样的一段评语:“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意思就是说连最擅长讽刺小说的鲁迅都赞赏能写下《儒林外史》的吴敬梓是中国小说史上讽刺小说的开山之祖。
“两茎灯草”引发的冤案古今中外总有相似之处,连小说情节也免不了俗。巴尔扎克笔下那个临死前都想把教士的镀金十字架拽下来据为己有的葛朗台就是个十足的“吝啬鬼”、“守财奴”。

这样一看,两茎灯草非得挑掉一根才能瞑目的严监生是个“小气鬼”的事看起来就是板上钉了钉。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课本中就节选了严监生的这一片段为课文,题为《临死前的严监生》。
原文片段如下(第六回):话说严监生临死之时,伸著两个指头,总不肯断气,几个侄儿和些家人,都来讧乱著问;有说为两个人的,有说为两件事的,有说为两处田地的,纷纷不一,却只管摇头不是。赵氏分开众人,走上前道:“老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盏灯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
可是诸位,这严监生真的就是一个吝啬鬼吗?毕竟作者在整本《儒林外史》中从未明言过任何一个人的褒贬优劣,文中人物全凭着读者的感觉来评说。人死如灯灭,这没说出口的遗愿真的就如赵姨娘对外人说的那样是唯恐费了油?
活在哥哥阴影下的严监生《儒林外史》中最先登场的是严监生的哥哥严贡生。需要向列位说明的是严贡生,严监生可并不是这两兄弟的名字而是身份。通俗来说贡生是老考不上举人的秀才,靠年纪熬上来的,相当于举人级别;大概可以举蒲松龄为例,当然聊斋先生的人品和名望远非严贡生可及的就是了。而严监生原名严大育,字致和,监生是花钱买的,相当于秀才级别。注意呀,严监生这里可是花了钱的,对于他来说这笔钱更不可能是一个小数目,仅仅是为了获得一个监生的名头。
即使这样,在出生时间还有行走身份上,身为哥哥的严贡生还是都压了严监生一头。
危急时刻对家人的大方其一,兄弟阋墙是真的,体现在两兄弟金钱观的极大反差上。在严监生眼中严贡生是坐吃山空的典型:“家兄寸土也无,人口又多,过不得三天,一买就是五斤,还要白煮得稀烂;上顿吃完了,下顿又在门口赊鱼。当初分家,也是一样田地,白白都吃穷了。”“如今甚至“端了家里梨花椅子,悄悄开了后门,换肉心包子吃”。
可当严贡生惹了两桩官司后逃到了省城,五个儿子也能跑的跑,能躲的躲,反而使得官差来向严监生要人,这时倒是严监生“留差人吃了酒饭,拿两千钱打发去了”。
其二,对于发妻王氏,王氏病重,他花重金为其延医问药,“每日四五个医生用药,都是人参附子”;妻子死后,“修斋、理七、开丧、出殡、用了四五千两银子”;妻子在世时,他将每年典铺内送来的三百两利钱给王氏作私房钱,也不追究她具体怎么开支;妻子死后给舅爷每人两封银子以作赶考的盘缠费等。
其二,穷什么不能穷教育,苦什么不能苦了孩子。“逐日夫妻四口在家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当小儿子要吃时,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同时为了让妾生的儿子名正言顺而扶正赵姨娘时上下打点,赠与舅爷每人一百两银子另加一些首饰;扶正赵氏,花了五十多两银子,大摆二十多桌酒席。
对自己吝啬导致了死亡妻子王氏死后严监生一次无意间发现了妻子平日里舍不得花攒下的钱,又念及往日里夫妻的情分,不由得痛哭失声,乃至郁结于心。再加上平时的吃穿极为节俭,病重时,“饮食不进,骨瘦如柴”,却仍“舍不得银子吃人参”。实在是可悲又可叹。
最令人叹息的是他有意无意间使得赵氏气死了病重的发妻王氏,两任妻子中王氏生时节俭死后也为他攒下了大笔金钱;而赵氏在他死后“掌管家务”,“钱过北斗,米烂成仓,奴仆成群,牛马成行,享福度日”。
怎不使人感叹?
隐藏在数字“二”后的不为人知的含义《儒林外史》中称严监生是个“胆小有钱的人”,为人处世处处低调。而在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对科举八股极为重视的明代。他最大的遗憾无疑便是一生都身份低下,委屈求全。
病重时,他才终于在舅爷面前说明:“我死之后,二位老舅照顾外甥长大,教他读读书,挣着进个学,免得象我一生,终日受大房的气。”在严监生的心中,既有未进学的遗憾,又有在需处处以长房为尊的压抑。
“两茎灯草”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含义?先不管临死之人究竟还能不能视物,还是看清小小的一盏油灯。更何况一茎灯草在上面那些严监生的慷慨花钱中也是不值得一提的罢。

可见严监生等的不是去拨掉那一根灯草,而是需要赵氏来拨,是需要这个家最后的女主人来承诺她会保住一个诺大的家财,保住严监生懵懂的幼子成才,来摆脱兄长一直以来带给严监生的阴影罢?可是这些在环绕在病榻前五个“生狼一样的”侄子们面前又怎么能明言?而赵氏那句“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在严监生面前无疑是一个暂时可以安心的承诺。
即使这样,赵氏在他死后仍是没有保住财产,反被严贡生打官司得了去,当然这就是另外的一番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