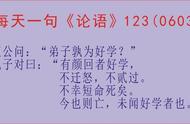2014年,由古代文学课学生作业结集成册的《琅叶集》
那是我最后一学期认真地上课。更换了老师后,在接下来的学期里,我几乎再也没去听过古代文学课,把所有时间耗在了图书馆里乱逛,读小说,直到收到了同学转达的其他教授的警告——这个人如果再不来上课的话,就不要参加考试了。
对谈
(侥幸毕业两年后,兔老师与那个成天翘课的壁虎同学又一次相遇。大家都还是老样子:她还是穿着长裙和她那买了五双穿了七年的rockport的超轻鞋,壁虎同学还是每天读着不知道来自哪个国家的外国小说,自娱自乐地做着选题。在外面有不少蚊子的夏天咖啡馆里,《诗人十四个》里的场景重新让他们回到了江南大学的蠡湖、雪浪山和长广溪,想起了春天的课堂和古代诗人的文学课)
中国诗词中的主流与另类
宫子:搜肠刮肚后,发现我喜欢的古代诗人还是有几个,比如说,柳永,姜夔,秦观。有一阵子还喜欢李贺和李白来着。但看得很少,我一首完整的诗词也背不上来。像陶渊明和杜甫这一类的诗人,我倒是理性上知道他们写的很好,但就是没那么喜欢。这种选择倾向是不是有些奇怪?
黄晓丹:其实这倒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的猜测是,欣赏陶渊明、杜甫、苏轼的诗,它其实不是一个完全自然的事情,它需要一种经过中国传统文化驯化的情感。我们很难靠天然的本性去喜欢它。比如说柳永那种“多情自古伤离别”或者秦观那种“有情芍药含春泪”,无论你是一个中国人、一个拉美人、一个巴尔干人还是阿拉伯人,都能够理解。那就是人情和自然之美的直接的触动。但陶渊明,以及我们中国文化中认为更“高雅”的那一类作者,比如苏轼、王维,什么是“种桑长江边,三年复当采”,什么是“长恨此身非我有”,什么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都需要包括时代背景、哲学思想的讲解,而在这些讲解中,还有一层是建立在历史和哲学的背景之上,而光讲历史和哲学却仍旧不能抵达的,就是境界。那境界是什么呢?我觉得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一个诗人将他的人生际遇、人格力量和对历史哲学的思考转化成一种审美化表达的能力。
如果只有那些际遇、思考,但是转化不成美不行,但如果只有美的形式,却没有背后真实的支撑也不行。一个人是不可能天生能对江边一棵杂树、湖边一只傻鸟思接千古,并读取出背后各种历史文化的蕴含的,更不可能跳过历史文化的思维过程,直接产生某种准确、细微的情感的,不然我们就生活在一个想象泛化和情绪泛滥的精神病性世界里了。
那么“驯化”是什么呢?就是通过长期的后天养成,熟悉我们这个文化传统中那些知性内容-审美内容-情感内容的既定链接,甚至可以跳过文本背后的知性内容,直接获得情感的触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看到诗话里写某人获某残句,反复讽咏,大为感动,而不知其本事为何,多年后知其本事,才确认当年的感觉没错。既可以说这是一种文学直觉的训练,也可以说这是文化对人的驯化。

黄晓丹
宫子:看来是我太不中国了。
黄晓丹:没有没有。确实你被驯化得越多,你就越能理解那种情感,但我并不觉得没有经过这个驯化就是个多么不好的事。说个好玩的事,前不久我去言几又给一个朋友的新书发布会捧场,那个书店的经理非常想好好招待我们,他看我是个女生,就和我说“等下他们谈的那本书看起来很难的,你可能会觉得很无聊,不如跟我去做香水吧”,于是我就去上了一节香水课。香水课的老师说了个很好玩的事。他说:“为什么大家都说薰衣草有助眠的功能,西方的助眠喷雾都是薰衣草味的?那是因为西方人习惯在洗衣过程中加入薰衣草,所以当他长大出门在外,焦虑难眠时,在枕头上喷点薰衣草香水,就好像回到了家里。中国人要是做睡眠喷雾,得用檀香皂或者六神吧”。我被他的智慧惊呆了,因为我出门的时候真的往包里塞了一小瓶檀香木精油。气味的驯化和文字的驯化没太大区别,甚至更顽固,但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规定每个人都使用同一种气味入眠呢?
有些像你这样的小朋友,在初中或者高中时代,在文化荒芜的环境里自己找到了一些获取知识的渠道。有的读了很多中国文学、有的读了很多日本文学,像你这样的是比较奇怪的,反正我对你读的那些作家只有一个印象,就是都住在和中国不通直航的地方。这样一种野蛮生长,带来的是对文学非常自主、广阔的接触,当然会带来欣赏眼光的不同。你今天在书评周刊做记者,终于把在课桌下面看闲书变成了职业,而且可以更随心所欲地挖掘世界边边角角的作家,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良性的自我驯化,我一点都不觉得想要把你掰回去学习唐诗。
宫子:有可能是这样。不过我还是挺喜欢柳永的,柳永那么潇洒的词人,在中国历史上真的太罕见了。
黄晓丹:非常少。我发现你喜欢的中国古代词人,都有种共性。要么像柳永和姜夔,没有做上什么官;要么像秦观,虽然做了官,却不在词里表达士大夫的感慨。和你谈话很有意思,因为你这样一说,我反观我喜欢的诗人,都更多地在作品里表达了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文化教养和审美品位,尤其是审美品位,我喜欢陶渊明、王维、晏殊,可能都是这个原因。
中国诗歌史中有诸如“雅郑”“正变”这些话题,审美批评的主流也还是温柔敦厚。你喜欢的那些基本是非主流。在中国诗歌的审美方面我很传统,就是喜欢温柔敦厚、明丽修洁的,要我讲李贺、讲柳永我就很痛苦,这可能也是驯化的结果吧。

诗人陶渊明画像。
宫子:对,李贺我也喜欢。我不喜欢那种“香草美人”寄托家国情怀的传统,我觉得那非常单调。
黄晓丹:“士大夫”首先是一个阶层,然后是一种身份意识,再后是一种审美习惯。这个阶层首先在社会层面消失了,但身份意识会在阶层实体消失之后继续存在很久,我身边就有很多不是读古典文学但具有士大夫精神的人。我有一个公务员朋友,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因为他的所有业余时间都用来写作他对于国际形势的观察、对于教育问题的思考,希望有朝一日可以上达天听,对社稷黎民有益。所以上次他来无锡体检,虽然下着暴雨,我还是把他带到了东林书院,在“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对联前照了相。你说的“家国情怀”、“香草美人”更多还是在身份意识层面,但我觉得会持续更久的是审美习惯。比如现在网上会流传雍正和乾隆审美品位对比的有趣文章,大部分中国人看了都会会心一笑,这就是这种审美品位的遗留。说不定你可以给你关心的那些住在各种奇怪地方的作家设计一套测试题,看看他们的审美是更接近乾隆还是雍正,他们对中国人能感受到的“雅”是何种感受?
宫子:可能我喜欢的都更加个人化一点。
黄晓丹:在现代以前的社会里,一个人不太可能以一个个体的方式生活。大部分作者以士大夫的身份生活,等到明代之后,书籍出版市场发达了,作者才可能以畅销书作家的身份写作,像冯梦龙之类的,但他们主要写的文体也变成了小说和随笔。你说的这点很有意思,如果我们做老师的罔顾学生自己身份认同,一定要摁着他们去为士大夫的家国情怀感动,这也是挺费劲的。理想的状况是向学生介绍更多的古典文学作品和读法,让学生能找到和自己匹配的作品。
“传统文化热”与个人的阅读选择
宫子:但现在好多人觉得,不理解这些古典文学,不理解传统文化,就不是个真正的中国人。
黄晓丹:为什么人们有时候会怀疑自己不是中国人?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除了中文,并没有掌握一门其他语言,也没有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置有房产、拥有护照,如果你不是中国人,还能是哪国人?文学性的语言有时候听起来很有情感的冲击力,比如“不会背唐诗宋词,就不是中国人”“没见过黄河长江,就不是中国人”。但事实是,这个国家幅员如此辽阔,从墨脱到黑河,总有人没有见过黄河长江、不会背唐诗宋词,但他们仍然还是中国人。我们要警惕对于“中国”概念的狭隘化。当然从深里来说,从鸦片战争以来,在整个近代因为中国饱受冲击,自我认同受损,常常处于“自我神话”和“自我贬低”循环往复的分裂性认同中。这就像青年人总是一会儿觉得自己天纵英才,一会儿觉得自己是块废柴。但随着个人和国家的成熟,更稳定的认同出现,“我到底是谁”的焦虑就会减轻。

李白,中国唐代大诗人。
宫子:可还是有很多极为“迷恋”传统文化的。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那种每天穿着古装去上课,写古诗,连发个朋友圈都要用文言文的同学。
黄晓丹:有啊有啊。对我来说这是个很纠结的事啊。我是个爱美的人,所以我觉得穿汉服也好,穿旗袍也好,穿西服也好,都要穿得美才行。但在日常生活中汉服穿得美的人是极为少见的。
我觉得有以下几个原因:一,看香奈儿的传记就知道,现在服装工业是极简化的机器生产,找到了成本和审美之间的最佳比值,而汉服要美,从设计到面料到手工,花费远远高于时装,以购买现代时装的预算购买汉服,那肯定是不会好看的呀;二,服装需要和环境相匹配,现代城市其实已经改变了人们观看的方式。比如我们看现代建筑,看它的体量、造型、立面、光影关系,而不是看细节的雕梁画栋,而几乎所有国家的古代服饰之美,都是建立在绫罗绸缎的颜色搭配和细节的绣花上的。
在大体量、远距离观看的现代都市中,欣赏汉服之美需要调整观看方式,所以我还是更愿意在博物馆和舞台上看汉服;第三说个接地气点的,在现实中,我就没见过人穿汉服而不搞折衷,所以我见过穿着耐克鞋穿汉服的
(因为要走路)
、披散头发穿汉服的
(因为不会梳头)
、背着书包穿汉服的
(因为没有书僮)
。所以我掂量了一下,决定还是不要穿汉服了,虽然有人说我头大,穿汉服应该还是蛮好看的……
宫子:作为一个教古代文学的老师,你怎么看有些像我这样的学生不爱学这门课?我这样的学生是不是还是少数?
黄晓丹:学还是要学的,不然考试考不出怎么拿毕业证书?但在考及格能毕业的基础上,要大家都吃饭也看杜甫这不现实。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书可以看,我们不会质问人家为什么没看过《伊利亚特》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什么一定要质问人家为什么没看过某唐代诗人的作品?他不喜欢这个诗人,也许他喜欢那个诗人;他不喜欢文学,可能他喜欢语言学;他对所有中文系的课都不喜欢,可能他喜欢当程序员。这都不要紧,只要他自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就好了。
而且我觉得越是有求知欲的学生,就越不能均等地对待每一门课,因为这里有精力分配的问题。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某个学生自己有非常开阔的阅读视野,那就意味着想在另外一个领域吸引他的注意力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对于他来说,有那么多好看的东西,我为什么还要花时间听你讲。这可能就是发生在你身上的情况。但大部分的学生不是这样的。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文学课是他们的课程安排中比较有趣、比较与个人生活有关系的课程,不管是古代文学、现代文学还是外国文学都是如此。相比公共课和语言类课程,我觉得文学类课程想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还是比较容易的。
如何在现代讲解古典诗歌?
宫子:据你观察,学生最喜欢哪些古代诗人?
黄晓丹:当他们从中学毕业进入大学时,最喜欢的诗人基本就是纳兰性德、李后主、李白、苏轼。在大学古代文学课的学习过程中,曹植、晏几道、黄仲则也会比较容易接受。
宫子: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黄晓丹:这些诗人基本都是青春诗人、激情诗人,从人生体验上来说与青年人接近,而且行文比较直白,阅读起来也没有太多障碍。当然苏轼是个例外,苏轼基本是人见人爱。学生比较难以理解陶渊明和王维,但我有一个有趣的观察,在我最新教的这一届,是00后的学生了,他们可以非常快地接受王维。有时我在想,这难道是因为真的进入“低*时代”了吗?当然这还要观察。而且对诗歌的阅读品位也是会不断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