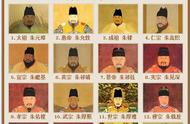然而实际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长城其实大部分是明朝修建的,而秦汉时期的长城比我们现在看到的长城要往北推进很多。东汉末年的吕布是五原郡九原县(今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麻池镇西北)人,也就是说在当时内蒙古大部分地区实际上是以定居农耕作为生活模式的汉人聚居的地区。气候的变化使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分界线开始逐渐南移,于是明代的长城就压缩到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位置上,基本上北京就已处于农牧分界线附近了,而在秦汉时期乃至更早的春秋战国时代北京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地区。

为什么唐代以后游牧民族开始强势崛起?事实上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比耶律阿保机、完颜阿骨打、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等人更有力量。从唐末宋初开始的气候变化一直持续到了明末清初,而明末清初恰好正处于小冰河期的峰值。现在一般推测明末的气候特征应该是比较寒冷干燥的。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而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不言自明的。崇祯皇帝登基后华北地区遭遇了持续四年的大旱,整个华北地区在那些年里几乎就是颗粒无收。

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既然老百姓找不着吃的,那么他们就只有到处逃亡,看看其他地方能不能找到吃的。还是由于气候的变化使明朝与蒙古大体上就以如今的长城一线作为持续博弈交锋的战线。如果我们暂时抛开明末这一特定时期不提,那么实际上整个有明一代两百余年最大的外患不是女真而是蒙古。在长期的战争过程中双方边境就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犬牙交错状态。现在既然在老家找不到吃的,那么自然也就有一部分华北地区的灾民涌入到与蒙古交界的地带讨生活。

这些逃荒的难民在草原上将牧场开垦成农田,这就破坏了牧场的生态环境,生活在草原的老鼠生存空间受到压缩,人与老鼠接触的机率随之大幅增加。据当地的地方志记载:崇祯六年山西兴县爆发鼠疫。当时的人不知道细菌学、病毒学,他们只是看到有人患病身亡。他们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死的,恐慌的人群为躲避瘟疫开始逃亡,而这恰恰导致了瘟疫的进一步扩散。难民们面对着瘟疫与饥荒的双重折磨:他们一路走来遇到的几乎全是灾民,他们找不到任何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