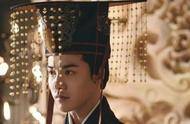1月24日上午8时12分,历史学家戴逸的百岁人生画上了句号。
历史像车轮滚滚向前,曾喟叹“个体生命对历史、对未来视程有限”的戴老此刻终能扶摇而上,俯瞰历史的车辙。
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近代何以落在西方国家后面?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何以如此坎坷曲折?中国在近几个世纪内达到了怎样的历史伟绩,又丧失了哪些历史机遇?中国有没有走一条更加便捷、畅通道路的可能……这些并无一致定论、曾困扰着历史学家们的“斯芬克斯之谜”,戴老会不会在俯瞰中豁然得解?
天地不语。
“我不同意‘史料即史学’,我主张经世致用”“历史的因铸成现实的果”“史学不是对策学”……戴老曾说过的话,依旧在尘世间一记一记敲击人心。
让我们重温文汇报于2019年7月14日刊出的通讯《戴逸:专骛清史愈久弥醇》,致敬这位史学家的史心史德。
【人物档案】
戴逸,1926年9月出生于江苏常熟,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
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图书馆馆长、清史研究所所长、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史学会会长。现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
戴逸是中国清史学界领军人物,著有《中国近代史稿》《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简明清史》《乾隆帝及其时代》《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清通鉴》等40多部著作。
2002年,我国《清史》纂修工程正式启动,戴逸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2013年,戴逸获得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戴逸:专骛清史愈久弥醇
本报驻京记者江胜信
位于北京张自忠路的段祺瑞执政府旧址,入口处一块“中国人民大学”的牌匾无声诉说着历史的变迁。清康熙九贝子府、清雍正和亲王府、北洋政府海军部、段祺瑞执政府……这栋建筑两百多年间所承担的皇亲府邸、军政要地的功用,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发生转变:1950年,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将这里作为校舍;1978年,其主楼由清史研究所使用;2006年,它被评定为国家级文保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