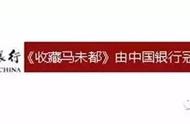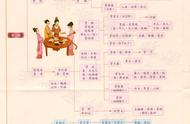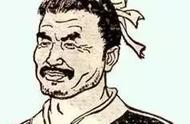最终,赵州桥于1958年修缮完成。
对此,梁思成很是不解,在他看来,桥体表面完全可以用原来的旧石贴面。
就算是有些地方需要更换,那也可以用其他拆下来的旧石料代替,“使整座桥恢复‘健康’、坚固,但不在面貌上‘还童’、‘年轻’。”

其桥面的整体翻新、建筑材料的大范围更换,让人痛心疾首。
现代工艺确实重现了赵州桥的原貌,但却没有承载它原有的历史。
1963年,梁思成故地重游再次考察赵州桥,对修缮结果表示极大不满。
他直言道:“直至今天,我还是认为把一座古文物建筑修得焕然一新,犹如把一些周鼎汉规用擦铜油擦得油光晶亮一样,将严重捐害到它的历史、艺术价值。……在赵州桥的重修中,这方面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

赵州桥的此类情况,倒让我想起在哲学里这样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如若将一艘船的零件一个接一个更换掉,等到旧零件全部更换为新零件,这艘船还是之前的那艘船吗?
此问题名为“忒修斯之船”,直至现在,对于此问题的答案,哲学家们还在争论不休。

“忒修斯之船”没有答案,但文物修复却有着一个明确答案,毕竟船没有意义,而古代文物却寄托着涓涓历史,蕴藏着千年烟火。
梁思成曾在文章中这样说道:
“我们须对各个时代之古建筑,负有保存或恢复原状的责任。在设计以前须知道这座建筑物的年代,须知这年代间建筑物的特征;对于这建筑物,如见其有损毁处,须知其原因及其补救方法;
须尽我们的理智,应用到这座建筑物本身上去,以求现存构物寿命最大限度地延长,不能像古人拆旧建新,于是这问题也就复杂多了。”